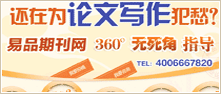论体裁指称距离
时间:2013-10-28来源:易品网 点击:
次
内容提要 指称距离问题并非歌词特有,而是由人类文化的“体裁约定性”造成:各种性质的词语的指称距离本来就有差异,在不同的体裁中则出现整体性的延长或缩短,最后形成“体裁指称距离阶梯”;在各种社会交流性体裁中,歌词的指称距离最长,这种现象造成了歌词的风格特征,以及歌词特有的构造与理解方式,例如姿势语、“拟声达意”、全不取义“兴”、褒义倾斜等。
1、指称距离问题
《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段话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研究,学界至今对此却没有一个能服众的解释。“诗言志”暂且不谈,什么是“歌永言”?《乐记》曰:“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歌”是一种“长言”。那么,什么是“长言”?一般解为“歌把朗诵的声调加以延长。”
本文提出一个看法,这“长言”既是物理形态的发声音长,也可以指另外一种“长”言,即语言的指称距离拉“长”。指称是“一个词语所表征的思想或事物”,即词语与其意指对象之间的关联方式。一般的逻辑语言,科学语言,实用语言,它们的语言方式尽量把指称距离缩短,即词语优先指向外延对象的潜力,词语的解释靠拢外延对象的趋势,这种潜力和趋势有利于高效率的理解。
在文学语言中,散文与小说的语言,指称方式依然比较接近日常话语。而诗的语言效果就建立在指称距离延长之上,因此常被称为“非指称性语言”。对比之下,歌的语言指称距离延长最为明显,经常明显地跳过外延对象。
虽然歌的语言在很多方面与诗的语言类似,经常并称为“诗歌语言”,从语言指称距离上来说,歌比诗长得多,主要原因是歌通过音调唱出,表达方式奇特。可以说,歌的指称距离,是所有语言表意体裁中最长的,可能只比呓语、梦话短一些,但呓语梦话并非交流语言,不必在社会交流领域中考虑。因此,本文提出:“歌永言”即“长言”,实有二义:可以指声调拖长,也可以指由此造成的指称距离延长。
语言的指称距离变异,并不是仅仅在各种体裁中才出现,各种词语的指称距离原本就不一样:特指名称指称距离最近,如人名、地名、年代名、建筑名等;指称能力稍远的是类别名称,如物种名称(桃子、蜥蜴等);而一些想象的物名,指称就落空,这就是符号学上所谓的“指称难题”,即有其言而无其物,例如凤凰、麒麟。一旦各种名称与“摹状词”结合成词组,其指称距离就更复杂,例如“盛唐气象”,两个词均有比较确切的指称,一旦合在一道,就可能指称相当不清楚。问题更复杂的是:许多名称言通意顺,却完全找不到指称,如罗素喜欢举的例子:“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头”。这不是说这些词语没有意义,而是说它的意义往往是内涵义,即皮尔斯符号学说的“解释项”。钱锺书建议用《史记》的用语,称艺术语言为“貌言华也”,因为它们有意牺牲直指意义,跳过了指称。
本文要讨论的是另外一种指称距离差异,即体裁引发的整体性指称距离延长。在不同体裁中,因词语性质造成的指称距离差别依然会保留,但体裁使其中所有的词语指称距离都发生变化。例如:不管是在什么体裁中,如果不加特别的修饰处理,“今日英国女王”总是比“今日法国国王”指称距离近;“2002年的第一场雪”总是比“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指称距离近,如果唱在歌里,它们的指称距离都会拉长(下文将有详细例子)。也就是说,在一个文本中,两种指称距离——词语本身的指称距离与体裁造成的指称距离——是混合的。某种体裁中所有的词语,比另一种体裁的同样词语,指称距离都更长或更短,本文称之为“体裁指称距离”。
维特根斯坦说:“音乐的表达方式:不要忘记一首诗不是用在提供信息的游戏中的,哪怕它是按信息的语言构成的”。文化体制决定了这类体裁(诗与歌)并不提供确切指称信息,因为体裁拉长了其中语词的指称距离。
2、乐音对指称的影响
歌的指称距离特别长与歌的特殊表现方式有关。语言和音乐在“声音媒介”上相通,歌词作为一种声乐语言,跨越并拥有了这两种声音:可以读出来,也可以唱出来,唱时出现音节的声学性延伸。《毛诗序》中描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言”只是最初的表义语言,通过“嗟叹”(加人情感的吟诵),继而通过“永歌”加入艺术的歌唱,达到情感表达过程。推动“言”到“嗟叹”到“永歌”这系列动作转化的内在动力,在宗白华看来,是人的内在情感。“今天我们所说的语言、吟诵、歌唱。其含义正与个人所说的‘言’、‘嗟叹’、‘永歌’相同……由语言而吟诵,由吟诵而歌唱,其间有着一贯的关系。”“逻辑语言,由于情感之推动,产生飞跃,就要‘长言之’和‘嗟叹之’(如腔和行腔)。这就到了歌唱的境界。”
一旦进入歌唱,歌词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音”。正如苏珊·朗格所说:“歌词进入音乐时,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便瓦解了。它的词句、声音、意义、短语、形象统统变成音乐的元素,进入一种全新结构,消失于歌曲之中,完全被音乐吞没了。”苏珊·朗格说“歌词完全被吞没”可能有些过于夸大音乐对歌词的作用,但至少她说对了一点:歌词一旦进入音乐曲调,语言就被乐音“重建”了。这一点,中国古人也早就论述过。《毛诗序》道:“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礼记·乐记》:“乐者,心之动;声者,乐之象;文采节奏,声之饰也。”所谓“声成文”,所谓“文采节奏”,都是指语言被音乐修饰而变形。
宋代的沈括也谈到过歌中语言的音乐重建问题,他提出了中国歌唱艺术的一条重要规律:“声中无字,字中有声”:
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凡曲,止是一声清浊高下如萦缕耳,宇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当使字字举本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块,此谓“声中无字”,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度”是也。如宫声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善歌者谓之“内里声”。不善歌者,声无抑扬,谓之“念曲”;“声无含韫,谓之”。
“字中有声”,即赵元任所说的语言和音乐的四个相通:赵元任认为,语言和音乐的区隔并不严格,两者都有音调的性质,声调(声高)的变化,都有音长,音量。在汉语中,语言和音乐之间至少有这四种共同的媒介形式,它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更像一个统一体。这两种形式在结构上互相回应。
而“声中无字”,并不是说歌唱中要把“字”完全取消,而是将字的音节融化在乐音中,即把“字”剖开,化成为“腔”。“字”的清晰表意(直接指称距离)被否定了,但歌的特殊表意方式在歌唱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取消了“字”(拉长了指称距离),却把它提高和充实了,这是一种“扬弃”,是一种辩证的否定。
戏曲表演里讲究的“咬字行腔”,也体现了这条规律。“字”和“腔”是中国歌唱的基本元素。咬字要清楚,因为语言表达内容。但为了充分的表达,还要从“字”引出“腔”。就如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所说,“咬字就如猫抓老鼠,不一下子抓死,既要抓住,又要保存活的。这样才能既有内 容的表达,又有艺术的韵味”。
所以,作为一般语言的歌词一旦进入到歌唱境界中,它的声音,甚至意义都被重建了:歌词就成了一种特殊的表意符号。
3、体裁与指称距离
詹姆逊指出,体裁“基本上是文学的‘机制’,或作家与特定公众之间的社会契约,其功能是具体说明一种特殊文化制品的适当运用”。我们看到,人类所有的符号表意行为,都被文化体制置于一种特定的体裁(或亚体裁)中。体裁是一种文化契约,它不仅是文化程式化的中介,而且作为中介又进一步固定符号发出者的程式化表意以及接收者的文化约定所规定的理解方式。
换言之,采用某个体裁,就决定了最基本的表意和接收方式。例如接收者听到一句话“我爱你”,他必须马上明白这句话的文化体裁类别:面对面的说话,信件结尾的问候,集体歌咏,KTV中的演唱等。然后才能解读出这是有确切指称的语句,还是某种曲折隐晦的表达,语义上有怎样不同的指称距离。依此明白应如何理解此语,当真,半当真,还是不当真:理解方式不完全取决于语句,也不完全取决于他的个人解释,而取决于体裁。
歌词是一种特殊的符号表意行为,诗的语言由于韵律,已经不太自然一歌词远比诗更甚;它依靠不同的音程,用非自然(非正常发音)的方式唱出来。一般的歌词创作要求“依乐章结构分篇,依曲拍为句,依乐声高下用字。其为之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而有定格的形式”。这种非自然的表现方式,一旦被固定下来,就成为一种体裁。歌词体裁,固定了歌词约定的最基本表意模式与解释模式。
歌词文本本身,不可能脱离这种体裁的文化契约支撑。在表意模式上,正因为歌曲基本上是一种公众性的交流方式,是一种非自然的演说形式,歌词语言的指称意义,与它的字面意义保持了很大的距离。沿用上面的例子,表意者想说“我爱你”,又想避免唐突的尴尬,想用暧昧的烟幕便于必要时逃遁,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三个字唱在歌里,因为歌词在所有交流语言体裁中,具有最远的指称距离。著名词家李宗盛有一首颇有双关意味的歌:“往事并不如烟/是啊/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可惜恋爱不像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写给自己的歌》)他感叹的是歌与现实中“恋爱”一语的指称距离很不同。
在解释模式上,歌词也期待接收者按体裁规定的方式得到解释,这很类似于卡勒所说的“体裁期待”:“同样的语句,在不同的体裁中,可产生不同的意义”。因此,“各种文学体裁不是不同的语言类型,而是不同的期待类型……戏剧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把某些作品当做戏剧来阅读的期待,与读悲剧和史诗完全不同”。卡勒指出:非指称性是诗这种体裁的“四个期待”之一,接收者的头脑不是白纸一张,任凭符号文本往写出意义,接收者首先意识到与文本体裁相应的形式,然后按这个体裁的一般要求,给予特定方式的“关注”。文化的训练使接收者在解释一首诗时,不会把“我燃烧”当做真的着火,而“我燃烧”在一首歌里,离真实的燃烧更远。
这样似乎形成一个悖论的循环定义:一首歌之所以为一首歌,主要原因就是它属于歌的体裁,它强迫读者按照歌的读法来理解它。“诗之所以为诗,是因为它属于诗这个体裁,它强迫读者用读诗的方法来读它”。如果有人坚决不按歌的方式来理解歌,歌就不成其为歌。
体裁对指称的整体性影响,这是学界,不管是语言学还是符号学,一直没有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一篇科学报告、哲学论文这些体裁的语言指称距离,差别不是很大。一篇美文、一篇小说,就不同了,因为语言风格已经“不自然”。而到了诗与歌这样的体裁中,情况就更为不同。不管原先的指称情况如何,进入诗这样不正常的文体,进入歌这样扭曲表达的体裁,所有的词语的指称性都会发生变异。
因为这种指称距离集体延长,歌词就需要一定的风格才能保证理解。明人王骥德这样总结,“世有不可解之诗,而不可令有不可解之曲”:
(歌的)句法,宜婉曲不宜直致,宜藻艳不宜枯瘁,宜溜亮不宜艰涩,宜清俊不宜重滞,宜新采不宜陈腐,宜摆脱不宜堆垛,宜温雅不宜激烈,宜细腻不宜粗率,宜芳润不宜噍杀。
清人李渔也认为:
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贱粗俗。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而后得意之所在者,并非绝妙好词。
这两个人的评论,是说歌词(戏曲唱词)“贵浅不贵深”,要求歌词语言浅平。因为他们明白歌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体裁,它的表意模式对语言品格的要求。在这一点上,歌词与诗很不相同:诗的语言可以靠隐晦复杂拉开指称距离,而歌词语言平浅,表面似乎是为“听懂”,实际上是抵消“体裁指称距离延长”,如果歌词风格过于艰涩,指称距离就可能过远。
4、歌词指称的一般化
在歌词中,即使是特殊性最强的特指专用名称,也会一般化而变成泛指。抗战期间,《太行山上》这首歌不仅在太行山根据地唱,实际上在全国各地都唱。“太行山”这个特殊的根据地名称,转而可以指任何坚持抗战的地方。抗战时期另一首著名的叙事歌《二小放牛郎》,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五十周年的一部专题片中,曾有这样一段文字:“在整个军队与平民庞大的伤亡数字中,也包括一位叫做‘王二小’的中国孩子”。“王二小”这个歌词中的少年英雄是否真实存在?此文列出很多争议,文章的最后并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说法,但总结颇有深意:“王二小是真有其人,还是一个综合了无数少年英雄的化身,对于这首歌曲的艺术价值和流传价值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王二小”在歌中已经不再作为一个特殊的人名,而是泛指小英雄。
中国20世纪90年代广泛流传的一首歌《小芳》,也有这样的指称性一般化效果。“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在回城之前的那个晚上/你和我来到小河旁/从没流过的泪水/随着小河淌”。词曲作者李春波最初的创作意图是献给知青时代的一位农村女友,但当歌曲流传时,这个“小芳”泛指为所有因男方的“前程”而分离的女性恋人了,现在甚至指进城的农民工留在家乡的女友。
这种意义播散,在“自然的”体裁中偶尔也会出现,比如在过多社会复用而造成象征化时(例如网络复用)。但在歌词中却很普遍,台湾歌手兼词曲作者郑智化的《阿飞和他的那个女人》中的“阿飞”。这个男性,一旦唱到歌中,就可以被任何类似的诨名所取代。解释问题,在理论上一直是很困难的课题,美国批评家斯坦利·费许的“解释群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理论,引发巨大争议。但对于歌曲这样的“社群艺术体裁”来说,“解释群体”理论比较合理:歌词指称距离延长,是解释群体的共同意见:没有一个听者一传唱者会认为“阿飞”是特指某个人。
歌词的这种指称距离延长现象,在仪式歌曲中最为典型。《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原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义勇军指的是“东北抗日义勇军”。1949年此歌被确定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时,就有人提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内容已经过时,特指的场景已经过去,此歌保留为《代国歌》,等待今后正式的国歌。三十年后,内容应当更加过时,但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确定其为国歌。又过了三十年,在2009年陕西两会上,政协委员李玉先对其中的歌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代战争“不需要冒着炮火前进,不提倡冒着炮火前进,也没必要冒着炮火前进”,并建议以《2009阅兵曲》作为新的国歌,其词云“中国军队不可阻挡”,贴近当今的现实。在同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一致认为,现行版应该保留。为什么国歌越过时越合适?倒不是因为代表们都理解本文说的指称距离延长理论,而是大家都敏感地觉得国歌“承载着民族的士气,背负着不可忘记的历史”,这个解释是久长的,因为指称已经虚化。
仪式歌,尤其是各种民族经久流传的各种仪式歌,比如哈尼族妇女出嫁时的哭嫁歌(哈尼语“迷威威”、或“然迷苏咪依威”),最早的内容是哈尼族妇女对传统婚姻的悲愤抗议,现在仅仅是出嫁仪式过程之一。“月兰”是流传在新疆维吾尔族的一种民间仪式歌曲,它至今依然用在婚礼、割礼等喜庆场合,也只是仪式而已,歌的具体内容已经不太相干:仪式性使用的时间越久,这些仪式歌的语词指称距离越远,甚至完全消失。
5、类语言化的“姿势语”
歌词中有一种特殊的常用语,即“类语言”。类语言是意义不太明确的情感符号,被认为是语言的起源形态。它因生命的原始律动相呼应而含有音韵,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原始歌词的诞生。在语言发展出较完整的体系后,类语言因为指称不明确,甚至连写法也不固定,从而被边缘化,这在任何一种民族语言中都是如此。
很多类似于“类语言”的原始歌谣以及魔咒神喻,都是“一种原生的意义、原生的逻辑,一种渗透了情绪和表象的意义,一种含韵在行为与活动中的逻辑”。鲁迅曾说:“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盖惟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而已。声音繁变,寝成言辞,言辞谐美,乃兆歌咏。”《吕氏春秋》卷六《音初》篇中记录的四方之歌,东音《破斧》歌:“呜呼!有疾,命矣夫!”一首命运之歌,实词只有两个,其他的多是感叹语气词。最早的南音《候人》歌:“候人兮猗!”只有一句,几乎全是语气词。闻一多考证后认为,此歌实为二字歌,后二字只是摹音,是因感情激荡而发出的声音。闻一多强调,这种声音“便是音乐的萌芽,也是孕而未化的语言。声音可以拉得很长,在声调上也有相当的变化,所以是音乐的萌芽。那不是一个词句,甚至不是—个字,然而代表一种颇复杂的涵义,所以是孕而未化的语言”。
《诗经·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浏兮,舒忧受兮,劳心骚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陈仲凡在分析此诗时指出,“其‘兮’字为和声,乃初民一面舞蹈,一面歌唱的风谣,和云南苗人的‘跳月舞’的诗相似……兴之所至,情之所钟,则发于喉舌,调节以手足而成乐歌”。其中的字韵的摹声效果“至今读之,如闻当时男女欢呼叫啸之声”。这是一种由“原始音乐”发展出来的“原始文学”。
纵观中国歌词史,从《诗经》到元曲到当代歌词,类语言不仅一直保留在歌词语言中,而且一些具有实指意义的语句,都可以类语言化,这就是所谓的“姿势语”。
“姿势语”这个概念,是由美国文论家R.P.布拉克墨尔提出的,他的定义却不是很明确:“语言由词语构成,姿势由动作构成……反过来也成立:词语形成动作反应,而姿势由语言构成——语言之下的语言,语言之外的语言,与语言并列的语言。词语的语言达不到目的时,我们就用姿势语……可以进一步说,词语的语言变成姿势语时才最成功。”为什么“词语的语言变成姿势语时才最成功”?布拉克墨尔的阐释是,“文字暂时丧失其正常的意义,倾向于变成姿势,就象暂时超过了正常意义的文字”。为此他举出的例子为莎士比亚《麦克白斯》中著名台词:“明天、明天、明天……”,以及《李尔王》的词:“决不,决不,决不,决不,决不……”。布拉克墨尔说,这两句,如果改成“今天,今天,今天……”和“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指称完全不同,而意义相近,因为在这里“文字已摆脱了字面意义而成为姿势。”
“姿势语”“丧失”字面意义,或者超越字面意义,变成一种姿势的效果,实际上是诗的指称距离延长到极点造成的效果。布拉克墨尔认为,词语此时“非常接近音乐”,因为“音乐属性……即是姿势,音乐的其他属性不过是表示姿势的手段”。词或词组在特殊语境下,可以超越语言的指称义,进入意义模糊的“音乐姿势”状态。
如此描写的姿势语,看起来像语言魔术,其实在现代歌中经常见到,比如易韦斋作词,萧友梅作曲的《问》:“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华年如水?你知道秋声添得几分憔悴?垂!垂!垂!”最后的三个“垂”字,意义超出了字面以外,而是凭借“拟声”表现一种气势,行文自然,与主题切协,令人忘记这个词实际上丢开了指称。同样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末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最后的“进“字,也具有同样效果。
钱锺书研究《诗经》后,称这种现象为“拟声达意”——“声意相宣(the soundas echotothe sense),斯始难能见巧。”钱锺书此说,至今注意者不多。用语音拟声,是正常的语言功能,用语音拟意,却是一种特殊的用法。索绪尔承认拟声词有初度指称性,即语音像似性,但他没有看到,在某些使用方式中,拟声词并不拟声,而是拟“意”。这种词句没有指称性(因为“意”并没有声音,无法“拟”),从而带上抽象意义。
钱锤书指的是《诗经》中大量表达状态或心情的词:杨柳依依、灼灼其华,拟的不是声,而是状态。诗经中大量形容“忧心”的词:“忧心炳炳”、“忧心奕奕”、“忧心殷殷”、“忧心钦钦”等,是对“忧心”的“拟音”。它们几乎可以用任何同韵叠字替代,因为都表达“忧心”,不是它们自己的语义指称,而是上下文的规定。后世的民间歌曲,有许多新的拟声达意词。元曲唱词中的大量叠字,至今读来依然非常生动:死搭搭,怒眸畔,实辟辟,热汤汤,冷湫湫,黑窣窣,黄晃晃,白洒洒,长梭梭,密拶拶,混董董。这些叠字可以用其他词替代,因为自身无指称。在当代歌曲中,这种“拟声达意”已经成为常规用法:从《嘻唰唰》(花儿乐队演唱),到《忐忑》(龚琳娜演唱),从个别语词,到整首歌,都明显地在推远指称距离,成为一种几乎是纯语音的感情外露,反过来,又获得了超出意义的抽象性。
6、全不取义“兴”
最极端的非指称化,出现于中国歌词中历史悠久的技巧“兴”。《说文解字》云,“兴,开头也”。在一首诗的开头,或一章诗的开头起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先描绘某种事物构成一个悬念,用以引发所要咏唱的内容。“兴”必须靠后面的咏才能起作用,因此,“先言他物”与“所咏之词”之间形成呼与应的关系。 关于“兴”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大抵有两种看法,第一种为兴包含“比”。《文心雕龙》认为“兴”是“托物起兴”;梁代钟蝾《诗品》中认为“文有尽而意有余,兴也”;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中认为,“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如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也,皆兴辞也”。宋人苏辙认为后世看不到比,是因为历史变了,先签的语义丢失,他在《栾城应诏集诗论》指出。“夫兴之体,犹云其意尔,意有所融乎当时,时已去而意不可知,故其类可以意推而不可以意解也”。从汉以来,大部分学者主相关论,因为《诗经》被尊崇为典籍,主张“微言大义”(也就是指称过多)的经学家附会,使关于“兴”的讨论误入歧途千年之久。
关于“兴”的另一种观点是以朱熹代表的“全不取义”论。“兴者,所以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因所见闻,或托物起兴,而以事继其后,诗之兴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义。”郑樵的观点和他接近:“凡兴者,所见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理义求也”。
说“兴”与正文意义无任何关联,也就是说“兴”词句的指称性脱落。许多“兴”只是提供一个语音(音韵与节奏)的呼唤,让诗的正文应和。正如郑樵说:“《诗》之本在声,声之本在兴”。五四后,越来越多现代学者赞扬“无关兴”原则,古史辩派更主无关论,钟敬文早年就建议把“兴诗”分为两种,一是只借物以起兴,和后面的歌意不相关的,命之为“纯兴诗”,二是借物起兴、隐约中兼略暗示其后面歌意的,命之为“兴而略带比意的诗”。顾颉刚说,他开头弄不明白“兴”。“数年后,我辑集了些歌谣,忽然在无意中悟出兴诗的意义。”启发他的是苏州民间唱本中的两句词:“山歌好唱起头难,起好头来就不难。”只要起头,无须关联。因此,“‘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它最重要的意义,只在‘洲’与下文‘逑’的协韵”。朱自清同意这个看法,说“起兴的句子与下文常是意义上不相续,却在音韵上相关连着”。钱锺书引阎若璩《潜邱答记》解《采苓》,首句“采苓采苓”,下章首句“采苦采苦”,“乃韵换耳无意义,但取音相谐”。钱锺书又把这个原则用于后世歌谣中,汉《饶歌》“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一般解首句为指天为誓的“天也”,而钱锺书认为是“有声无意”的发端兴呼,类似“一二一”之类现代儿歌的起首。
歌词中“兴”的功能重在作出情调性的呼,导入并烘托感情,所以“兴”并一定需要关联,也就是摆脱上下文需要的指称性。比兴是中国传统诗歌和歌谣常用的表现手法。后世歌词的发展,使“全不取义兴”减少到偶然一用,现代歌词更是如此。但一旦用上了不相关“兴”,就会很有味,因为它提供了比较古老的《诗经》式呼应结构。例如这首陕南民歌《芹菜韭菜栽两行》,开首与全歌的内容不相关联:“月亮出来亮堂堂,芹菜韭菜栽两行;郎吃芹菜勤思姐,姐吃韭菜久想郎。”另一首土家族民歌《葡萄不熟味不甜》:“初三初四月不圆,葡萄不熟味不甜;火烧巴茅心不死,不见情郎心不甘。”无根据的“兴”的确是中国味特别浓厚,呼语与应语之间没有比喻关系,而且这两首歌的首句可以被其他诗句替代,无法解释出一个“深意”,证明的确出现失去指称性现象。
7、歌词的褒义倾斜
歌词的理解,有一种特殊的心理文化机制,这就是“褒义倾斜”,接收者会尽可能向善意方面解释。正是歌词中语词的指称距离延长,才使褒义倾斜成为可能。所谓“说的比唱的还好听”,通常是用来讽刺说大话夸海口,胡乱允诺而并不准备兑现的话语。这话却从反面揭示了歌词的指称距离:同样词句如果在其他体裁中,意义阐释方式会很不相同,因为是在歌里,就尽量往好的方面想:相比而言,歌词的语句要求明显的“乌托邦解释”,即接受者带上善意的、美好的、理想的色彩来宽容地理解。
这样的例子很多。《大阪城的姑娘》是一首求婚歌。歌词中有句“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赶着那马车来”。求婚语句却够荒唐的:“嫁妆”,“马车”已经够贪婪,还要“带上你的妹妹”。但此歌之所以经久流行,原因之一在于歌词阐释的“褒义倾斜”机制,接受者不会往不道德的方面去想,只是觉得有些诙谐。
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中唱道:“我愿做一只小羊,依偎在她身旁,我愿她拿着细细的长鞭,轻轻地打在我身上。”歌词一旦写下来读,很有点受虐狂倾向。但此歌是中国流行歌中的不朽名曲,没有人觉得此歌词性倾向怪异。
而歌词中的过分夸张,似乎更是常态“美化”。比如马来西亚歌手阿弟作词作曲的华语歌曲《小薇》,“我”向小女孩允诺,“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看那星星多美丽,摘下一颖亲手送给你”。词句花言巧语,夸大其词,只有在歌词才不会被取笑。
谭咏麟演唱的《披着羊皮的狼》,用“狼”和“羊”来类比恋人的情感,有些令人惊栗:“梦中惊醒,我只是想轻轻地吻吻你,你别担心,我知道想要和你在一起,并不容易,我们来自不同的天和地,你总是感觉和我一起,是漫无边际阴冷的恐惧。我真的好爱你,我愿意改变自己。”由于歌词尽现“狼”的温柔和执着,加上歌众心理的“褒义倾斜”,让“狼”的意义非外延化,添上新的内涵。
同样的效果,也出现在一些含有露骨性爱内容的歌中,歌不像诗那样可以通过语言的婉转曲折,把性写得模糊隐晦。一般说,歌词虽然充满欲望,却很少直接写性,即使性事偶然出现在歌词中,也是隐约且褒义化的。比如许巍的《在别处》:“就在我进入的瞬间,我真想死在你怀里。我看到我另一个身体,漂向另一个地方”。歌是“我对你”的诉求,此时歌就必须依靠指称距离实现美化。冯梦龙搜集整理的歌谣集《山歌》(亦称《童痴二弄·山歌》),共十卷,383首,其中370余首与“私情”有关,却被赞誉为“明代一绝”,正是得益于歌的阐释褒义倾斜机制。在当代歌曲中,情歌至今占绝大多数:两性关系中原先容易引起误解,甚至反感的言辞,一旦出现在歌词中,都会朝好的方面理解。
这种“褒义倾斜”,原因并不复杂,因为歌的“意动”目的是正向的,是请求接受者朝歌者所希望的方向作反应。而歌的词句之指称距离,使歌词得到这种语义优势。因为体裁定型化,歌的语句对性别关系处理方式,会向社群的期盼靠拢。
本文描述的种种歌曲语言魔术——姿势语、“拟声达意”、全不取义“兴”、褒义倾斜等——之所以可能,正在于歌词的“长言效果”,即歌词的语句指称距离,被体裁的文化规定性拉长。
可以简略地概括说:科学、新闻、历史、散文、哲学、小说、诗歌、歌词等语言交流形式,组成了一个指称距离的体裁阶梯。这个差别是我们文化的程式所构成的,个别作品中的具体安排,只能在这基础上作局部调整。关于体裁形成的指称距离,至今尚未见到任何讨论,连语言学界都没有提及。本文讨论的只是歌词的指称距离延长,结论却触及人类文化整体性的“体裁指称距离阶梯”。本文的任务,不是为如此大规模的文化现象找出规律性原因,先录于此,以待方家指正。不过歌曲的确处于这个阶梯的一端,“指称距离延长”最为明显。也最为戏剧化,这是值得我们歌词研究者仔细讨论的。
1、指称距离问题
《尚书·尧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这段话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研究,学界至今对此却没有一个能服众的解释。“诗言志”暂且不谈,什么是“歌永言”?《乐记》曰:“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歌”是一种“长言”。那么,什么是“长言”?一般解为“歌把朗诵的声调加以延长。”
本文提出一个看法,这“长言”既是物理形态的发声音长,也可以指另外一种“长”言,即语言的指称距离拉“长”。指称是“一个词语所表征的思想或事物”,即词语与其意指对象之间的关联方式。一般的逻辑语言,科学语言,实用语言,它们的语言方式尽量把指称距离缩短,即词语优先指向外延对象的潜力,词语的解释靠拢外延对象的趋势,这种潜力和趋势有利于高效率的理解。
在文学语言中,散文与小说的语言,指称方式依然比较接近日常话语。而诗的语言效果就建立在指称距离延长之上,因此常被称为“非指称性语言”。对比之下,歌的语言指称距离延长最为明显,经常明显地跳过外延对象。
虽然歌的语言在很多方面与诗的语言类似,经常并称为“诗歌语言”,从语言指称距离上来说,歌比诗长得多,主要原因是歌通过音调唱出,表达方式奇特。可以说,歌的指称距离,是所有语言表意体裁中最长的,可能只比呓语、梦话短一些,但呓语梦话并非交流语言,不必在社会交流领域中考虑。因此,本文提出:“歌永言”即“长言”,实有二义:可以指声调拖长,也可以指由此造成的指称距离延长。
语言的指称距离变异,并不是仅仅在各种体裁中才出现,各种词语的指称距离原本就不一样:特指名称指称距离最近,如人名、地名、年代名、建筑名等;指称能力稍远的是类别名称,如物种名称(桃子、蜥蜴等);而一些想象的物名,指称就落空,这就是符号学上所谓的“指称难题”,即有其言而无其物,例如凤凰、麒麟。一旦各种名称与“摹状词”结合成词组,其指称距离就更复杂,例如“盛唐气象”,两个词均有比较确切的指称,一旦合在一道,就可能指称相当不清楚。问题更复杂的是:许多名称言通意顺,却完全找不到指称,如罗素喜欢举的例子:“当今法国国王是秃头”。这不是说这些词语没有意义,而是说它的意义往往是内涵义,即皮尔斯符号学说的“解释项”。钱锺书建议用《史记》的用语,称艺术语言为“貌言华也”,因为它们有意牺牲直指意义,跳过了指称。
本文要讨论的是另外一种指称距离差异,即体裁引发的整体性指称距离延长。在不同体裁中,因词语性质造成的指称距离差别依然会保留,但体裁使其中所有的词语指称距离都发生变化。例如:不管是在什么体裁中,如果不加特别的修饰处理,“今日英国女王”总是比“今日法国国王”指称距离近;“2002年的第一场雪”总是比“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指称距离近,如果唱在歌里,它们的指称距离都会拉长(下文将有详细例子)。也就是说,在一个文本中,两种指称距离——词语本身的指称距离与体裁造成的指称距离——是混合的。某种体裁中所有的词语,比另一种体裁的同样词语,指称距离都更长或更短,本文称之为“体裁指称距离”。
维特根斯坦说:“音乐的表达方式:不要忘记一首诗不是用在提供信息的游戏中的,哪怕它是按信息的语言构成的”。文化体制决定了这类体裁(诗与歌)并不提供确切指称信息,因为体裁拉长了其中语词的指称距离。
2、乐音对指称的影响
歌的指称距离特别长与歌的特殊表现方式有关。语言和音乐在“声音媒介”上相通,歌词作为一种声乐语言,跨越并拥有了这两种声音:可以读出来,也可以唱出来,唱时出现音节的声学性延伸。《毛诗序》中描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言”只是最初的表义语言,通过“嗟叹”(加人情感的吟诵),继而通过“永歌”加入艺术的歌唱,达到情感表达过程。推动“言”到“嗟叹”到“永歌”这系列动作转化的内在动力,在宗白华看来,是人的内在情感。“今天我们所说的语言、吟诵、歌唱。其含义正与个人所说的‘言’、‘嗟叹’、‘永歌’相同……由语言而吟诵,由吟诵而歌唱,其间有着一贯的关系。”“逻辑语言,由于情感之推动,产生飞跃,就要‘长言之’和‘嗟叹之’(如腔和行腔)。这就到了歌唱的境界。”
一旦进入歌唱,歌词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音”。正如苏珊·朗格所说:“歌词进入音乐时,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便瓦解了。它的词句、声音、意义、短语、形象统统变成音乐的元素,进入一种全新结构,消失于歌曲之中,完全被音乐吞没了。”苏珊·朗格说“歌词完全被吞没”可能有些过于夸大音乐对歌词的作用,但至少她说对了一点:歌词一旦进入音乐曲调,语言就被乐音“重建”了。这一点,中国古人也早就论述过。《毛诗序》道:“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礼记·乐记》:“乐者,心之动;声者,乐之象;文采节奏,声之饰也。”所谓“声成文”,所谓“文采节奏”,都是指语言被音乐修饰而变形。
宋代的沈括也谈到过歌中语言的音乐重建问题,他提出了中国歌唱艺术的一条重要规律:“声中无字,字中有声”:
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凡曲,止是一声清浊高下如萦缕耳,宇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当使字字举本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块,此谓“声中无字”,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度”是也。如宫声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善歌者谓之“内里声”。不善歌者,声无抑扬,谓之“念曲”;“声无含韫,谓之”。
“字中有声”,即赵元任所说的语言和音乐的四个相通:赵元任认为,语言和音乐的区隔并不严格,两者都有音调的性质,声调(声高)的变化,都有音长,音量。在汉语中,语言和音乐之间至少有这四种共同的媒介形式,它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更像一个统一体。这两种形式在结构上互相回应。
而“声中无字”,并不是说歌唱中要把“字”完全取消,而是将字的音节融化在乐音中,即把“字”剖开,化成为“腔”。“字”的清晰表意(直接指称距离)被否定了,但歌的特殊表意方式在歌唱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取消了“字”(拉长了指称距离),却把它提高和充实了,这是一种“扬弃”,是一种辩证的否定。
戏曲表演里讲究的“咬字行腔”,也体现了这条规律。“字”和“腔”是中国歌唱的基本元素。咬字要清楚,因为语言表达内容。但为了充分的表达,还要从“字”引出“腔”。就如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所说,“咬字就如猫抓老鼠,不一下子抓死,既要抓住,又要保存活的。这样才能既有内 容的表达,又有艺术的韵味”。
所以,作为一般语言的歌词一旦进入到歌唱境界中,它的声音,甚至意义都被重建了:歌词就成了一种特殊的表意符号。
3、体裁与指称距离
詹姆逊指出,体裁“基本上是文学的‘机制’,或作家与特定公众之间的社会契约,其功能是具体说明一种特殊文化制品的适当运用”。我们看到,人类所有的符号表意行为,都被文化体制置于一种特定的体裁(或亚体裁)中。体裁是一种文化契约,它不仅是文化程式化的中介,而且作为中介又进一步固定符号发出者的程式化表意以及接收者的文化约定所规定的理解方式。
换言之,采用某个体裁,就决定了最基本的表意和接收方式。例如接收者听到一句话“我爱你”,他必须马上明白这句话的文化体裁类别:面对面的说话,信件结尾的问候,集体歌咏,KTV中的演唱等。然后才能解读出这是有确切指称的语句,还是某种曲折隐晦的表达,语义上有怎样不同的指称距离。依此明白应如何理解此语,当真,半当真,还是不当真:理解方式不完全取决于语句,也不完全取决于他的个人解释,而取决于体裁。
歌词是一种特殊的符号表意行为,诗的语言由于韵律,已经不太自然一歌词远比诗更甚;它依靠不同的音程,用非自然(非正常发音)的方式唱出来。一般的歌词创作要求“依乐章结构分篇,依曲拍为句,依乐声高下用字。其为之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而有定格的形式”。这种非自然的表现方式,一旦被固定下来,就成为一种体裁。歌词体裁,固定了歌词约定的最基本表意模式与解释模式。
歌词文本本身,不可能脱离这种体裁的文化契约支撑。在表意模式上,正因为歌曲基本上是一种公众性的交流方式,是一种非自然的演说形式,歌词语言的指称意义,与它的字面意义保持了很大的距离。沿用上面的例子,表意者想说“我爱你”,又想避免唐突的尴尬,想用暧昧的烟幕便于必要时逃遁,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这三个字唱在歌里,因为歌词在所有交流语言体裁中,具有最远的指称距离。著名词家李宗盛有一首颇有双关意味的歌:“往事并不如烟/是啊/在爱里念旧也不算美德/可惜恋爱不像写歌/再认真也成不了风格”(《写给自己的歌》)他感叹的是歌与现实中“恋爱”一语的指称距离很不同。
在解释模式上,歌词也期待接收者按体裁规定的方式得到解释,这很类似于卡勒所说的“体裁期待”:“同样的语句,在不同的体裁中,可产生不同的意义”。因此,“各种文学体裁不是不同的语言类型,而是不同的期待类型……戏剧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把某些作品当做戏剧来阅读的期待,与读悲剧和史诗完全不同”。卡勒指出:非指称性是诗这种体裁的“四个期待”之一,接收者的头脑不是白纸一张,任凭符号文本往写出意义,接收者首先意识到与文本体裁相应的形式,然后按这个体裁的一般要求,给予特定方式的“关注”。文化的训练使接收者在解释一首诗时,不会把“我燃烧”当做真的着火,而“我燃烧”在一首歌里,离真实的燃烧更远。
这样似乎形成一个悖论的循环定义:一首歌之所以为一首歌,主要原因就是它属于歌的体裁,它强迫读者按照歌的读法来理解它。“诗之所以为诗,是因为它属于诗这个体裁,它强迫读者用读诗的方法来读它”。如果有人坚决不按歌的方式来理解歌,歌就不成其为歌。
体裁对指称的整体性影响,这是学界,不管是语言学还是符号学,一直没有注意的一个重大问题:一篇科学报告、哲学论文这些体裁的语言指称距离,差别不是很大。一篇美文、一篇小说,就不同了,因为语言风格已经“不自然”。而到了诗与歌这样的体裁中,情况就更为不同。不管原先的指称情况如何,进入诗这样不正常的文体,进入歌这样扭曲表达的体裁,所有的词语的指称性都会发生变异。
因为这种指称距离集体延长,歌词就需要一定的风格才能保证理解。明人王骥德这样总结,“世有不可解之诗,而不可令有不可解之曲”:
(歌的)句法,宜婉曲不宜直致,宜藻艳不宜枯瘁,宜溜亮不宜艰涩,宜清俊不宜重滞,宜新采不宜陈腐,宜摆脱不宜堆垛,宜温雅不宜激烈,宜细腻不宜粗率,宜芳润不宜噍杀。
清人李渔也认为:
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同看,又与不读书之妇人、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贱粗俗。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而后得意之所在者,并非绝妙好词。
这两个人的评论,是说歌词(戏曲唱词)“贵浅不贵深”,要求歌词语言浅平。因为他们明白歌词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体裁,它的表意模式对语言品格的要求。在这一点上,歌词与诗很不相同:诗的语言可以靠隐晦复杂拉开指称距离,而歌词语言平浅,表面似乎是为“听懂”,实际上是抵消“体裁指称距离延长”,如果歌词风格过于艰涩,指称距离就可能过远。
4、歌词指称的一般化
在歌词中,即使是特殊性最强的特指专用名称,也会一般化而变成泛指。抗战期间,《太行山上》这首歌不仅在太行山根据地唱,实际上在全国各地都唱。“太行山”这个特殊的根据地名称,转而可以指任何坚持抗战的地方。抗战时期另一首著名的叙事歌《二小放牛郎》,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五十周年的一部专题片中,曾有这样一段文字:“在整个军队与平民庞大的伤亡数字中,也包括一位叫做‘王二小’的中国孩子”。“王二小”这个歌词中的少年英雄是否真实存在?此文列出很多争议,文章的最后并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说法,但总结颇有深意:“王二小是真有其人,还是一个综合了无数少年英雄的化身,对于这首歌曲的艺术价值和流传价值已经不是那么重要”。“王二小”在歌中已经不再作为一个特殊的人名,而是泛指小英雄。
中国20世纪90年代广泛流传的一首歌《小芳》,也有这样的指称性一般化效果。“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在回城之前的那个晚上/你和我来到小河旁/从没流过的泪水/随着小河淌”。词曲作者李春波最初的创作意图是献给知青时代的一位农村女友,但当歌曲流传时,这个“小芳”泛指为所有因男方的“前程”而分离的女性恋人了,现在甚至指进城的农民工留在家乡的女友。
这种意义播散,在“自然的”体裁中偶尔也会出现,比如在过多社会复用而造成象征化时(例如网络复用)。但在歌词中却很普遍,台湾歌手兼词曲作者郑智化的《阿飞和他的那个女人》中的“阿飞”。这个男性,一旦唱到歌中,就可以被任何类似的诨名所取代。解释问题,在理论上一直是很困难的课题,美国批评家斯坦利·费许的“解释群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理论,引发巨大争议。但对于歌曲这样的“社群艺术体裁”来说,“解释群体”理论比较合理:歌词指称距离延长,是解释群体的共同意见:没有一个听者一传唱者会认为“阿飞”是特指某个人。
歌词的这种指称距离延长现象,在仪式歌曲中最为典型。《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原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义勇军指的是“东北抗日义勇军”。1949年此歌被确定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时,就有人提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内容已经过时,特指的场景已经过去,此歌保留为《代国歌》,等待今后正式的国歌。三十年后,内容应当更加过时,但1978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确定其为国歌。又过了三十年,在2009年陕西两会上,政协委员李玉先对其中的歌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代战争“不需要冒着炮火前进,不提倡冒着炮火前进,也没必要冒着炮火前进”,并建议以《2009阅兵曲》作为新的国歌,其词云“中国军队不可阻挡”,贴近当今的现实。在同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一致认为,现行版应该保留。为什么国歌越过时越合适?倒不是因为代表们都理解本文说的指称距离延长理论,而是大家都敏感地觉得国歌“承载着民族的士气,背负着不可忘记的历史”,这个解释是久长的,因为指称已经虚化。
仪式歌,尤其是各种民族经久流传的各种仪式歌,比如哈尼族妇女出嫁时的哭嫁歌(哈尼语“迷威威”、或“然迷苏咪依威”),最早的内容是哈尼族妇女对传统婚姻的悲愤抗议,现在仅仅是出嫁仪式过程之一。“月兰”是流传在新疆维吾尔族的一种民间仪式歌曲,它至今依然用在婚礼、割礼等喜庆场合,也只是仪式而已,歌的具体内容已经不太相干:仪式性使用的时间越久,这些仪式歌的语词指称距离越远,甚至完全消失。
5、类语言化的“姿势语”
歌词中有一种特殊的常用语,即“类语言”。类语言是意义不太明确的情感符号,被认为是语言的起源形态。它因生命的原始律动相呼应而含有音韵,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原始歌词的诞生。在语言发展出较完整的体系后,类语言因为指称不明确,甚至连写法也不固定,从而被边缘化,这在任何一种民族语言中都是如此。
很多类似于“类语言”的原始歌谣以及魔咒神喻,都是“一种原生的意义、原生的逻辑,一种渗透了情绪和表象的意义,一种含韵在行为与活动中的逻辑”。鲁迅曾说:“在昔原始之民。其居群中,盖惟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而已。声音繁变,寝成言辞,言辞谐美,乃兆歌咏。”《吕氏春秋》卷六《音初》篇中记录的四方之歌,东音《破斧》歌:“呜呼!有疾,命矣夫!”一首命运之歌,实词只有两个,其他的多是感叹语气词。最早的南音《候人》歌:“候人兮猗!”只有一句,几乎全是语气词。闻一多考证后认为,此歌实为二字歌,后二字只是摹音,是因感情激荡而发出的声音。闻一多强调,这种声音“便是音乐的萌芽,也是孕而未化的语言。声音可以拉得很长,在声调上也有相当的变化,所以是音乐的萌芽。那不是一个词句,甚至不是—个字,然而代表一种颇复杂的涵义,所以是孕而未化的语言”。
《诗经·陈风·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浏兮,舒忧受兮,劳心骚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劳心惨兮。”陈仲凡在分析此诗时指出,“其‘兮’字为和声,乃初民一面舞蹈,一面歌唱的风谣,和云南苗人的‘跳月舞’的诗相似……兴之所至,情之所钟,则发于喉舌,调节以手足而成乐歌”。其中的字韵的摹声效果“至今读之,如闻当时男女欢呼叫啸之声”。这是一种由“原始音乐”发展出来的“原始文学”。
纵观中国歌词史,从《诗经》到元曲到当代歌词,类语言不仅一直保留在歌词语言中,而且一些具有实指意义的语句,都可以类语言化,这就是所谓的“姿势语”。
“姿势语”这个概念,是由美国文论家R.P.布拉克墨尔提出的,他的定义却不是很明确:“语言由词语构成,姿势由动作构成……反过来也成立:词语形成动作反应,而姿势由语言构成——语言之下的语言,语言之外的语言,与语言并列的语言。词语的语言达不到目的时,我们就用姿势语……可以进一步说,词语的语言变成姿势语时才最成功。”为什么“词语的语言变成姿势语时才最成功”?布拉克墨尔的阐释是,“文字暂时丧失其正常的意义,倾向于变成姿势,就象暂时超过了正常意义的文字”。为此他举出的例子为莎士比亚《麦克白斯》中著名台词:“明天、明天、明天……”,以及《李尔王》的词:“决不,决不,决不,决不,决不……”。布拉克墨尔说,这两句,如果改成“今天,今天,今天……”和“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指称完全不同,而意义相近,因为在这里“文字已摆脱了字面意义而成为姿势。”
“姿势语”“丧失”字面意义,或者超越字面意义,变成一种姿势的效果,实际上是诗的指称距离延长到极点造成的效果。布拉克墨尔认为,词语此时“非常接近音乐”,因为“音乐属性……即是姿势,音乐的其他属性不过是表示姿势的手段”。词或词组在特殊语境下,可以超越语言的指称义,进入意义模糊的“音乐姿势”状态。
如此描写的姿势语,看起来像语言魔术,其实在现代歌中经常见到,比如易韦斋作词,萧友梅作曲的《问》:“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华年如水?你知道秋声添得几分憔悴?垂!垂!垂!”最后的三个“垂”字,意义超出了字面以外,而是凭借“拟声”表现一种气势,行文自然,与主题切协,令人忘记这个词实际上丢开了指称。同样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末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最后的“进“字,也具有同样效果。
钱锺书研究《诗经》后,称这种现象为“拟声达意”——“声意相宣(the soundas echotothe sense),斯始难能见巧。”钱锺书此说,至今注意者不多。用语音拟声,是正常的语言功能,用语音拟意,却是一种特殊的用法。索绪尔承认拟声词有初度指称性,即语音像似性,但他没有看到,在某些使用方式中,拟声词并不拟声,而是拟“意”。这种词句没有指称性(因为“意”并没有声音,无法“拟”),从而带上抽象意义。
钱锤书指的是《诗经》中大量表达状态或心情的词:杨柳依依、灼灼其华,拟的不是声,而是状态。诗经中大量形容“忧心”的词:“忧心炳炳”、“忧心奕奕”、“忧心殷殷”、“忧心钦钦”等,是对“忧心”的“拟音”。它们几乎可以用任何同韵叠字替代,因为都表达“忧心”,不是它们自己的语义指称,而是上下文的规定。后世的民间歌曲,有许多新的拟声达意词。元曲唱词中的大量叠字,至今读来依然非常生动:死搭搭,怒眸畔,实辟辟,热汤汤,冷湫湫,黑窣窣,黄晃晃,白洒洒,长梭梭,密拶拶,混董董。这些叠字可以用其他词替代,因为自身无指称。在当代歌曲中,这种“拟声达意”已经成为常规用法:从《嘻唰唰》(花儿乐队演唱),到《忐忑》(龚琳娜演唱),从个别语词,到整首歌,都明显地在推远指称距离,成为一种几乎是纯语音的感情外露,反过来,又获得了超出意义的抽象性。
6、全不取义“兴”
最极端的非指称化,出现于中国歌词中历史悠久的技巧“兴”。《说文解字》云,“兴,开头也”。在一首诗的开头,或一章诗的开头起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先描绘某种事物构成一个悬念,用以引发所要咏唱的内容。“兴”必须靠后面的咏才能起作用,因此,“先言他物”与“所咏之词”之间形成呼与应的关系。 关于“兴”的性质,历来众说纷纭。大抵有两种看法,第一种为兴包含“比”。《文心雕龙》认为“兴”是“托物起兴”;梁代钟蝾《诗品》中认为“文有尽而意有余,兴也”;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中认为,“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如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也,皆兴辞也”。宋人苏辙认为后世看不到比,是因为历史变了,先签的语义丢失,他在《栾城应诏集诗论》指出。“夫兴之体,犹云其意尔,意有所融乎当时,时已去而意不可知,故其类可以意推而不可以意解也”。从汉以来,大部分学者主相关论,因为《诗经》被尊崇为典籍,主张“微言大义”(也就是指称过多)的经学家附会,使关于“兴”的讨论误入歧途千年之久。
关于“兴”的另一种观点是以朱熹代表的“全不取义”论。“兴者,所以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因所见闻,或托物起兴,而以事继其后,诗之兴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义。”郑樵的观点和他接近:“凡兴者,所见在此,所得在彼,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理义求也”。
说“兴”与正文意义无任何关联,也就是说“兴”词句的指称性脱落。许多“兴”只是提供一个语音(音韵与节奏)的呼唤,让诗的正文应和。正如郑樵说:“《诗》之本在声,声之本在兴”。五四后,越来越多现代学者赞扬“无关兴”原则,古史辩派更主无关论,钟敬文早年就建议把“兴诗”分为两种,一是只借物以起兴,和后面的歌意不相关的,命之为“纯兴诗”,二是借物起兴、隐约中兼略暗示其后面歌意的,命之为“兴而略带比意的诗”。顾颉刚说,他开头弄不明白“兴”。“数年后,我辑集了些歌谣,忽然在无意中悟出兴诗的意义。”启发他的是苏州民间唱本中的两句词:“山歌好唱起头难,起好头来就不难。”只要起头,无须关联。因此,“‘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它最重要的意义,只在‘洲’与下文‘逑’的协韵”。朱自清同意这个看法,说“起兴的句子与下文常是意义上不相续,却在音韵上相关连着”。钱锺书引阎若璩《潜邱答记》解《采苓》,首句“采苓采苓”,下章首句“采苦采苦”,“乃韵换耳无意义,但取音相谐”。钱锺书又把这个原则用于后世歌谣中,汉《饶歌》“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一般解首句为指天为誓的“天也”,而钱锺书认为是“有声无意”的发端兴呼,类似“一二一”之类现代儿歌的起首。
歌词中“兴”的功能重在作出情调性的呼,导入并烘托感情,所以“兴”并一定需要关联,也就是摆脱上下文需要的指称性。比兴是中国传统诗歌和歌谣常用的表现手法。后世歌词的发展,使“全不取义兴”减少到偶然一用,现代歌词更是如此。但一旦用上了不相关“兴”,就会很有味,因为它提供了比较古老的《诗经》式呼应结构。例如这首陕南民歌《芹菜韭菜栽两行》,开首与全歌的内容不相关联:“月亮出来亮堂堂,芹菜韭菜栽两行;郎吃芹菜勤思姐,姐吃韭菜久想郎。”另一首土家族民歌《葡萄不熟味不甜》:“初三初四月不圆,葡萄不熟味不甜;火烧巴茅心不死,不见情郎心不甘。”无根据的“兴”的确是中国味特别浓厚,呼语与应语之间没有比喻关系,而且这两首歌的首句可以被其他诗句替代,无法解释出一个“深意”,证明的确出现失去指称性现象。
7、歌词的褒义倾斜
歌词的理解,有一种特殊的心理文化机制,这就是“褒义倾斜”,接收者会尽可能向善意方面解释。正是歌词中语词的指称距离延长,才使褒义倾斜成为可能。所谓“说的比唱的还好听”,通常是用来讽刺说大话夸海口,胡乱允诺而并不准备兑现的话语。这话却从反面揭示了歌词的指称距离:同样词句如果在其他体裁中,意义阐释方式会很不相同,因为是在歌里,就尽量往好的方面想:相比而言,歌词的语句要求明显的“乌托邦解释”,即接受者带上善意的、美好的、理想的色彩来宽容地理解。
这样的例子很多。《大阪城的姑娘》是一首求婚歌。歌词中有句“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赶着那马车来”。求婚语句却够荒唐的:“嫁妆”,“马车”已经够贪婪,还要“带上你的妹妹”。但此歌之所以经久流行,原因之一在于歌词阐释的“褒义倾斜”机制,接受者不会往不道德的方面去想,只是觉得有些诙谐。
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中唱道:“我愿做一只小羊,依偎在她身旁,我愿她拿着细细的长鞭,轻轻地打在我身上。”歌词一旦写下来读,很有点受虐狂倾向。但此歌是中国流行歌中的不朽名曲,没有人觉得此歌词性倾向怪异。
而歌词中的过分夸张,似乎更是常态“美化”。比如马来西亚歌手阿弟作词作曲的华语歌曲《小薇》,“我”向小女孩允诺,“我要带你飞到天上去,看那星星多美丽,摘下一颖亲手送给你”。词句花言巧语,夸大其词,只有在歌词才不会被取笑。
谭咏麟演唱的《披着羊皮的狼》,用“狼”和“羊”来类比恋人的情感,有些令人惊栗:“梦中惊醒,我只是想轻轻地吻吻你,你别担心,我知道想要和你在一起,并不容易,我们来自不同的天和地,你总是感觉和我一起,是漫无边际阴冷的恐惧。我真的好爱你,我愿意改变自己。”由于歌词尽现“狼”的温柔和执着,加上歌众心理的“褒义倾斜”,让“狼”的意义非外延化,添上新的内涵。
同样的效果,也出现在一些含有露骨性爱内容的歌中,歌不像诗那样可以通过语言的婉转曲折,把性写得模糊隐晦。一般说,歌词虽然充满欲望,却很少直接写性,即使性事偶然出现在歌词中,也是隐约且褒义化的。比如许巍的《在别处》:“就在我进入的瞬间,我真想死在你怀里。我看到我另一个身体,漂向另一个地方”。歌是“我对你”的诉求,此时歌就必须依靠指称距离实现美化。冯梦龙搜集整理的歌谣集《山歌》(亦称《童痴二弄·山歌》),共十卷,383首,其中370余首与“私情”有关,却被赞誉为“明代一绝”,正是得益于歌的阐释褒义倾斜机制。在当代歌曲中,情歌至今占绝大多数:两性关系中原先容易引起误解,甚至反感的言辞,一旦出现在歌词中,都会朝好的方面理解。
这种“褒义倾斜”,原因并不复杂,因为歌的“意动”目的是正向的,是请求接受者朝歌者所希望的方向作反应。而歌的词句之指称距离,使歌词得到这种语义优势。因为体裁定型化,歌的语句对性别关系处理方式,会向社群的期盼靠拢。
本文描述的种种歌曲语言魔术——姿势语、“拟声达意”、全不取义“兴”、褒义倾斜等——之所以可能,正在于歌词的“长言效果”,即歌词的语句指称距离,被体裁的文化规定性拉长。
可以简略地概括说:科学、新闻、历史、散文、哲学、小说、诗歌、歌词等语言交流形式,组成了一个指称距离的体裁阶梯。这个差别是我们文化的程式所构成的,个别作品中的具体安排,只能在这基础上作局部调整。关于体裁形成的指称距离,至今尚未见到任何讨论,连语言学界都没有提及。本文讨论的只是歌词的指称距离延长,结论却触及人类文化整体性的“体裁指称距离阶梯”。本文的任务,不是为如此大规模的文化现象找出规律性原因,先录于此,以待方家指正。不过歌曲的确处于这个阶梯的一端,“指称距离延长”最为明显。也最为戏剧化,这是值得我们歌词研究者仔细讨论的。
- 认准易品期刊网
1、最快当天审稿 最快30天出刊
易品期刊网合作杂志社多达400家,独家内部绿色通道帮您快速发表(部分刊物可加急)! 合作期刊列表
2、100%推荐正刊 职称评审保证可用
易品期刊网所推荐刊物均为正刊,绝不推荐假刊、增刊、副刊。刊物可用于职称评审! 如何鉴别真伪期刊?
都是国家承认、正规、合法、双刊号期刊,中国期刊网:http://www.cnki.net 可查询,并全文收录。
3、八年超过1万成功案例
易品期刊网站专业从事论文发表服务8年,超过1万的成功案例! 更多成功案例
4、发表不成功100%全额退款保证
易品期刊网的成功录用率在业内一直遥遥领先,对于核心期刊的审稿严格,若未能发表,全额退款! 查看退款证明
文学评论热门杂志征稿信息
- 上一篇:钱锺书早期的“异国形象”研究
- 下一篇:佛教思想与文学性灵说
发表流程

排行榜
- 推荐
- 点击
- 从批评性话语分析角度 06-01
- 论小说中工人形象研究 05-28
- 写给所有人的围城 05-28
- 是泛性还是人性的回归 05-29
- 最熟悉的陌生人中的女 05-29
- 浅析金锁记的语言魅力 05-28
- 霍尔无声的语言魅力浅 05-28
- 学科转型语境下的五四 10-28
- 审美化研究的图像学路 10-28
- 文化与自我白虎之拉康 05-29
投稿百科
写作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