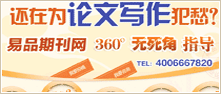第三人惊吓损害的法教义学分析
第三人惊吓损害的法教义学分析
基于德国民法理论与实务的比较法考察
侵权行为法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对受害人的损害填补,俾使其恢复到受害之前的状态,但与此同时亦须恰当划定损害赔偿的界限,以不过分限制加害人在人身和经济方面的发展空间。因此,侵权行为法须协调“权益保护与行为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1]本专题所讨论的“林玉暖案”所蕴含的“第三人惊吓损害”(Schockschaden Dritter)法律问题,突出地反映了上述侵权行为法的价值两难。[2]因此,如何平衡惊吓损害事件中加害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乃是各国侵权法理论与实践的重点与难点。[3]我国学界迄今尚未有较为全面的德国民法学说和实务的介绍评析,为此,笔者将依据德国侵权法的结构,梳理第三人惊吓损害的体系位置及具体责任构成要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德国民法关于该问题的价值判断,最后通过比较法的视角,检讨我国民法原理和实务裁判的得失。
一、从外部体系透视第三人惊吓损害在德国民法上的定位
德国民法方法论将法律体系分为外部体系与内部体系。所谓外部体系,是以抽象概念为基础,建构一种对法律素材清晰而概括的表达和区分结构,这种体系对于法律判决的可预见性和法律安定性具有积极意义。[4]而与此相对,隐含在法律制度内部的统一而有序的价值原则和意义脉络,构成了法律的内部体系。[5]外部体系能够指示个别概念和法律问题在整个体系中的应有位置,而且有助于辨识具体的案件事实涵摄于何种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之下,“熟悉(外部)体系的判断者能随即将事件划定范围,因为他能认识可得使用的规范所属的领域”。[6]基于此,对于本文拟解决的第三人惊吓损害的案型而言,将其置于何种法律视角和法律规范下予以考察,最佳的切入方法是判定其在外部体系中的位置。
(一)间接受害人?
首先须讨论的是,惊吓损害的受害人是否为侵权行为的“间接受害人”。这得依有关法律进行裁判。以惊吓损害的典型案件为例,通常是直接受害人的人身受侵害,其近亲属目睹或听闻噩耗,精神上受刺激或受惊吓,从而自身发生健康损害。正如“林玉暖案”的法院裁判理由所指出的:“受到直接伤害的是原告之子,而原告作为母亲目睹儿子被殴致血流满面而昏厥,是间接受害人”,健康权受损的间接受害人可对加害人享有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但德国民法理论对此存有不同观念。
尽管同一事件可能导致除直接受害人之外的第三人的损害,但并非因该事件引起的、凡具有相当因果关系的损害后果,均可请求赔偿。准确地说,在违反契约义务时的赔偿请求权人,是契约相对人或受契约义务保护的第三人,而在侵权行为中则是权益被侵害的受侵害人。[7]从《德国民法典》的侵权行为一般条款(BGB §§823, 826)来看,立法者将人身损害的诉讼原告资格限于直接受害人(primare Verletzten),而并未赋予受害人的亲属针对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8]但例外的是,根据《德国民法典》第844条和第845条,因受害人死亡而负担丧葬费,或丧失抚养请求权,或失去受害人劳务的第三人(通常是受害人的近亲属或继承人),作为间接受害人对加害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该请求权为间接受害人自身固有的请求权,因而上述条文可谓损害赔偿权利人的扩张。[9]可见,德国侵权法原则上不考虑间接受害人的损害赔偿,只在特别规定情况下允许第三人对加害人享有直接请求权。
基于上述原理,德国学者法恩克尔指出,虽然第三人因目睹或听闻直接受害人遭受人身伤害,发生精神惊吓并致健康损害,但由《德国民法典》第844条和第845条的立法目的可见,立法者仅将第三人对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限于法律明文规定的情况。因此,第三人就惊吓损害的赔偿请求权没有教义学上的根据。[10]但这种观点已被理论界和实务界所摒弃。权威的民法典评注书均认为,惊吓损害实质上是通过加害人对另一人(如近亲属)侵权行为的媒介而侵害到自己的健康(必须达到自身健康损害程度),因此惊吓损害根本不是“第三人损害”( Drittschaden ),恰是受害人自身的法益损害,如其符合《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构成要件,损害后果必须予以填补。[11]就此,拉伦茨指出,第三人通常遭受一般性经济损失(allgemeiner Vermagensschaden ),如其可得赔偿,将导致赔偿责任的无限扩大,应为法律所拒绝;相反,第三人惊吓损害,恰是受害人自身遭受第823条第1款意义上的“法益侵害”,第三人当然得为请求权人。[12]因此,惊吓损害不是赔偿权利人范围或加害人赔偿责任的扩张问题。[13]
事实上,德国法院向来认为惊吓损害的第三人是自身权利受侵害的当事人。1931年9月21日帝国法院(RG)对首例惊吓损害作出判决。该案中一位母亲因听闻其女儿因车祸去世,虽然其未亲历现场,但已然发生健康损害,因而原告请求加害人损害赔偿,法院支持诉求的判决理由指出:
间接损害是指某人自身并非侵权行为的受害人,而是侵权行为在该人财产上的反射后果。然而,就当下(惊吓损害)案件而言,原告因侵权行为而自身健康受到损害,其诉讼请求正是针对该健康损害。在帝国法院的实践中,从未声称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列举的法益和权利,必须是被直接侵害的、而间接的侵害不足以构成(侵权行为)。[14]
1971年5月11日德国联邦法院(BGH)在一起标志性的惊吓损害案件判决中,接受帝国法院的观点并指出:
(民法典)立法者认同,在亲历或听闻事故时发生不寻常的“损伤性(traumatisch)”影响而导致自身身体或精神/心理(geistig/seelisch)的健康损害,则该人享有独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帝国法院(RGZ 162, 321)完全清楚,在惊吓损害中,涉及的问题是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保护的法益受直接侵害(unmittelbare Verletzung),而并不是如同民法典第844条、第845条那般涉及间接损害的赔偿。[15]
由上可见,在德国民法学理与实务上,第三人惊吓损害之所以被称为“第三人”或“间接受害人”,只是相对于第一受害人而言。但其遭受的损害并非第844条、第845条意义上的“间接损害”,而是自身的身体健康所受损害。德国学者施密特指出:将第三人惊吓损害称为间接损害,这种不准确的表述有时会引发混乱。[16]总之,按德国民法通说,第三人惊吓损害不可与第844条、第845条间接损害相提并论,二者不能作相同或类似评价。
(二)健康损害、惊吓损害与第三人惊吓损害
德国民法中“损害”一词通常是指某种行为的责任后果及范围,准确地说“惊吓损害”问题的关键不是损害,而是“惊吓侵害”( Schockverletzung ),即以惊吓方式侵害他人第823条第1款所保护的法益。但“惊吓损害”已被用来固定地描述这种特殊的侵权责任问题,而且侵害往往伴随着损害,因此按德国民法的习惯用语,仍称为“惊吓损害”。[17]
惊吓损害须达到《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侵害健康程度,才能予以损害赔偿。“侵害健康”是指对人之内在生命过程的功能损害,它并不取决于人之器官和躯体的完整性是否受损(虽然身体侵害常常导致健康损害)。[18]此外,健康损害包括身体的或心理的疾病状态,身体疾病须借助医学知识查明,而心理病态须借助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的认知。后者虽然难以把握,但一般认为,如果人们对于事故、死亡等事件的惊恐、伤心、痛苦和情绪低落的反映,超出心理一社会的正常程度,就存在心理健康损害。[19]
“惊吓”(Schock,或休克),在医学上用来描述一种因某种事故而发生的急性循环障碍,其性质为短暂的,但也可能导致机体的损害。[20]法学上的界定与此不同,施密特指出:惊吓是“一种突然对个人产生影响、与心理有关的外界事件造成的心理故障或心理刺激。”在事故中受害人只要出现一种医学上可验明的身体上或/和心理上的反映,即构成“惊吓”。[21]因此,惊吓在法学上是指一种健康损害,[22]而且侵权法仅对那些达到一定强度并持续一段时间的惊吓损害考虑损害赔偿。作为一种健康损害状态,惊吓损害普遍存在,且不限于在第三人身上发生。[23]德国民法学理上,一般将惊吓损害大致分为如下三类。
其一,直接惊吓损害。此种损害不需以受害人的某种法益(如身体、健康、自由或所有权)损害作为媒介,而是因受害人特殊的心理敏感性对损害事件的心理反映而产生。[24]例如,因烟花爆竹的爆炸声而引起惊恐;因顾客在饮食中发现异物而产生恶心和忧虑;超市营业员怀疑顾客偷窃而对其大声呵斥或令其当众出丑,致使顾客受惊吓,等等。[25]这些惊吓如若请求损害赔偿,须达到明显的心理损害程度,且加害人之行为自由超出法律保护范围。除此之外,在人类共同生活中日常发生的、不可避免的惊吓,属于一般生活风险,如果一律予以损害赔偿,则个人的创造性将受阻滞。[26]
其二,作为某种法益损害后果的惊吓损害。上述直接惊吓损害不以某种法益损害为前提,与此有别,当受害人因自身其他的某种法益受侵害后,随即导致了该受害人的惊吓损害。[27]例如,受害人身体受伤出血因目睹鲜血而晕厥,即为侵害身体而引发惊吓损害。此外,因财产权受侵害也可能导致惊吓损害,例如,入室行窃者突然惊醒沉睡中的屋主,或因自己的宠物猫、狗突然被伤害致死而精神上受刺激。
作为法益损害后果的惊吓损害,与一般的法益损害后果的处理方式并无不同。德国民法理论和实务上认为,它本质上属于法益受侵害的损害后果范围,加害人原则上应予赔偿。例如,因伤害事故导致脊椎严重受损(身体侵害),受害人因长期承受伤痛而演化成心理疾病,并丧失劳动能力。[28]德国联邦法院对此类侵权后果指出:
如果某人因过失引起他人身体或健康之损害,且在责任法上应由其负责,那么,其责任也及于由此所生之损害后果(Folgenschaden)……对侵权行为所致心理(损害)后果的损害赔偿义务,并不必以器质性(损害)原因(organische Ursache)为前提,毋宁说,只要如下这一点能够确定就足够了,即如果没有发生事故就不会产生这种心理上的损害后果。此外,也不要求加害人对侵权行为所生之损害后果(损害范围)必须预见。[29]
由此可见,作为法益损害后果的惊吓损害,比较容易认定其相当因果关系,从而计人损害赔偿范围。此外,德国民法学说提出用“法规保护目的”来限制其责任范围。例如,受害人因身体伤害所致皮肉血肿或青瘀,而发生神经衰弱,进而导致两星期不能工作。由于这种轻微的身体损害不具有显著性,构成一般生活风险,因而不属于《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保护的利益范围。再者,因物之所有权受侵害而发生惊吓损害后果虽然普遍存在,但也不属于第823条第1款的保护范围。[30]
其三,第三人惊吓损害。德国民法文献中经常讨论的惊吓损害案例,是受害人(第三人)因经历、目睹或听闻他人遭受死亡或重伤,从而引发其自身的健康损害。[31]德国民法理论上认为,第三人惊吓损害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被认可,而是其界限在何处。[32]一般而言,第三人惊吓损害基本构成要件包括如下三方面:[33](1)惊吓损害必须基于明显的诱因(verstandliche Anlass),即第三人现场经历或事后听闻亲近之人因事故而死亡或重伤。如果事故仅造成身体轻伤害(如胳膊受伤)或物之损害(例如宠物狗死亡),或警察错误地通知其近亲属有犯罪嫌疑,均不产生第三人惊吓损害的赔偿请求权;[34](2)第三人所受损害超出正常承受的痛苦程度,构成健康损害,[35]如第三人尚未达到病理上须治疗的状态,单纯的因失去亲人的痛苦,不足以产生赔偿请求权;[36](3)第三人原则上须为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配偶、父母和子女)。
综上所述,惊吓损害是一种由心理原因引起的健康损害,包括直接惊吓损害、因法益受侵害引起的惊吓损害和第三人惊吓损害。虽然三者都表现为受害人的健康损害,但其责任问题的侧重点不同:第一种在于责任成立,第二种在于责任范围,第三种兼而有之。
(三)第三人之精神痛苦金请求权
第三人目睹或听闻亲人死亡或重伤而发生惊吓损害,有时仅表现出悲痛、哀伤、情绪低落等心理反应,尤其是近亲属死亡时的“丧亲之痛”[37]。那么,第三人可否就这种“纯粹精神损害”[38]请求赔偿痛苦金呢?在目前的德国民法中,这一诉求是无法得到满足的,[39]原因有如下三方面。其一,按《德国民法典》第253条(原第847条),精神损害痛苦金仅在身体、健康、自由或性自主受到侵害时,才可请求赔偿。近亲属因亲人的死亡或重伤,虽然承受巨大的心理悲痛,但如其自身没有发生法益损害,仍将无从请求痛苦金。其二,《德国民法典》第844条、第845条规定可赔偿的近亲属死亡的间接损害仅限于财产损失,并不包括精神损害痛苦金。其三,在未有明确立法的前提下,法院自然也不甘冒“续造法律”的风险,主动填补法律漏洞。就此,德国联邦法院认为,要求法院去衡量人的生命价值过于苛求,故而在判决中向来不支持这一诉讼请求。[40]
相较于欧洲其他各国,德国显然处于落后状态。例如,在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判例认可因亲人死亡或重伤所受之单纯悲痛可得赔偿;葡萄牙和意大利将赔偿限于亲属的死亡;英国、瑞士、希腊、波兰、荷兰等国家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奥地利、瑞典虽然没有通过法律明确规定,但其最高法院近年来也逐渐予以认可。通过比较可见,德国民法不保护近亲属死亡的纯粹精神痛苦,与欧洲各国的法律发展已经脱节。德国学者极不满意这种法制状况,称德国几乎是最后一个不承认这种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国家,这成为一个“时代错误”,甚至戏称德国为特立独行的“莫希干人”。[41]
有鉴于此,近年来理论界对德国损害赔偿法的改革呼声日益增加,为克服死者近亲属不能请求纯粹精神损害痛苦金的弊端,大致有如下三种思路。
第一,近亲属作为继承人可主张死者的精神损害痛苦金(BGB § § 823, 1922)。[42]即直接受害人在受伤至死亡的持续一段时间内,产生痛苦金请求权,并转移给继承人。[43]在1990年之前,因为痛苦金请求权具有高度人身性,除非以契约承认或发生诉讼系属,原则上不得让与和继承。1990年之后立法者消除了这种限制,当事人未承认或未有诉讼主张,痛苦金请求权也可让与和继承,并可计人遗产之中。[44]但这种方式的弊端在于:其一,死者的精神痛苦金很难认定,尤其在事故发生现场或在送医不久后即去世的情形下,受害人没有恢复意识状态,因此无从产生精神损害痛苦金;[45]其二,虽然死者的精神损害痛苦金请求权可以继承,但它毕竟不是抚慰近亲属本身的丧亲之痛。[46]
第二,第三人惊吓损害可令加害人对死者近亲属承担金钱赔偿义务(包括精神痛苦金赔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死者遗属不赔偿精神痛苦金的法律不公。[47]在此基础上,法院可以放低惊吓损害的门槛条件,使近亲属更容易获得赔偿。[48]但目前德国司法实务掌握其构成要件还是比较严格,尤其是第三人须达到健康损害程度这一要件,恰恰说明将该制度作为近亲属纯粹精神损害的功能替代正是其弊端所在。德国学者克林格借用奥地利最高法院的一件判决理由来批评该制度的不公正:
对近亲属所受之纯粹的情感损害不予赔偿的法律状况,越来越令人不满。痛苦是否伴随疾病而生,其界限经常存在问题。因子女死亡而悲痛的遗属父母着实难以理解:因为没有达到疾病状态,所以他们的痛苦金请求权被驳回,这属于他们自身应承担的一般性生活风险。轻微的身体伤害,例如瘀伤或扭伤,立即产生精神痛苦金请求权,然而失去近亲所致的纯粹心理悲痛(bloBeseeliche Schmerzen)—尽管这种痛苦通常会被强烈感受到—却不存在这样的请求权。[49]
由此可见,德国学者也认为,丧亲之痛是比一般的身体伤痛更为严重的精神痛苦,法律对一个轻度的人身伤害都赋予痛苦金赔偿,反而对一项更为严重的精神痛苦却视而不见,这的确有违“同等事务同等对待”的正义理念,并有教条主义之嫌。
第三,最根本的解决途径是承认近亲属在受害人死亡时自身遭受纯粹精神痛苦,即使尚未达到健康损害程度,也可主张痛苦金请求权。但因其欠缺请求权基础,故而学者建议以一般人格权作为近亲属纯粹精神损害痛苦金的请求权基础。克林格主张,近亲属的精神利益主要体现在与死者的家庭联系之中,鉴于德国《基本法》第6条有保护婚姻和家庭的价值理念,司法实务围绕家庭利益形成一组一般人格权精神损害赔偿的案例群。例如,母亲因医生误诊而导致孩子不当出生、因丢失精子致不能生育、破坏和阻止父亲与儿子建立联系等,均得依一般人格权主张痛苦金请求权。既然根据宪法产生的法秩序保护权利人的家庭计划不受侵犯,那么同样地,法秩序也应保护家庭现有状态免受他人侵权行为的破坏。因此,在受害人死亡或重伤时,其近亲属得基于一般人格权请求精神痛苦金赔偿。[50]但以上建议尚未形成理论通说,亦未见诸司法实践。
由上可见,第三人惊吓损害在德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部分替代了死者近亲属丧亲之痛的损害赔偿功能。但由于其构成要件过于严格,须以健康损害为前提,因而难以充分满足死者近亲属的赔偿请求。从积极意义来看,第三人惊吓损害不限于近亲属的死亡情形,而且包括重伤者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这有利于受害人近亲属的利益保护。
(四)小结
以上我们将德国民法上的第三人惊吓损害置于间接受害人、惊吓损害和第三人精神痛苦金的框架内分别予以考察。通过这种外部体系的认识,初步了解了第三人惊吓损害的产生来源、损害形态、构成要件及制度功能。由此明确,第三人惊吓损害并不涉及《德国民法典》第844条、第845条的间接损害赔偿问题,也不直接产生第253条所规定的精神损害痛苦金请求权。作为一种惊吓损害的特殊形态,它在本质上是第823条第1款意义上的健康侵权行为。
二、第三人惊吓损害侵权責任的结构检验
第三人惊吓损害既为一种独立的侵权责任形态,下文拟就该侵权行为的责任成立和责任范围逐项进行检讨分析。[51]德国民法学理通常按三阶段理论(Dreistufigkeit)认定侵权责任的成立,即行为的该当性(Tatbestand)、违法性(Rechtswidrigkeit)和有责性(Verantwortlichkeit);[52]如果侵权责任成立,继而考虑责任范围,即具体损害赔偿后果。因为三阶段论有助于准确判明侵权责任的成立要件,能够实现法律的安定性和明晰性。[53]因而下文依此方法,在《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侵害健康意义上,对第三人惊吓损害的责任成立和责任范围逐次分析检验。
(一)第三人惊吓损害的该当性
1.法益侵害
侵权行为的该当性系指受害人存在法益侵害,且加害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于此首先讨论法益侵害问题。
第三人因亲人死亡或重伤通常会遭受心理痛苦或精神打击,但并非都能成立侵权责任,只有那些造成第三人健康损害的情形才有可能产生责任。虽然德国民法理论和实务均明确认可对心理上的影响也构成健康损害,[54]但并非所有的第三人惊吓的心理后果都构成健康损害。为避免滥诉和责任泛化,须对其严格限制。由此,“侵害健康”成为过滤第三人惊吓损害侵权行为的第一层限制措施。[55]
健康损害一般是通过医学诊断即可判明的疾病状态。德国学说和判例对第三人惊吓造成健康损害的要件比较严格,一方面要求损害后果须有显著性和持续性,另一方面仅凭医学标准尚不能断定健康损害,还须辅助以“常人观念”。[56]德国联邦法院在1971年5月11日的裁判中指出:
(第三人惊吓造成的损害)不仅在医学的视角下,而且按常人观念,[57],也被看作身体或健康损害。因此,那些尽管在医学上被认为是损害,但不具有那种“惊吓特性”的健康侵害,也可能得不到赔偿。通常与令人悲痛的损害事件密切联系的、对人的健康状况并非轻微的影响,往往不构成一项独立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58]
据此,第三人的损害程度一方面符合医学上的健康损害标准,另一方面按“常人观念”,认为须超出通常的健康不良状况,才可获得赔偿。[59]换言之,如损害未超出听闻近亲属死亡所遭受打击的正常反应程度,则不受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保护。[60]由此可见,这种“健康损害”的界定已经不再是“定义”,而是对医学上成立的侵害健康概念附加了特别要件。这种附加要件的目的是限制第三人惊吓损害的责任范围,将加害人不可预见的痛苦、悲愤、沮丧等“通常反应”(normal Reaktion)排除出去。[61]但这种作法的负面后果在于,破坏了第823条第1款意义上“侵害健康”的概念统一性。[62]因此,近期有德国学者主张,第三人惊吓的健康损害与一般健康损害同样应采取医学上的判定标准。[63]至于第三人惊吓损害的责任限制和可归责性,可在随后的因果关系、违法性或有责性阶段予以检验。
2.受害人
第三人惊吓损害事件中存在两方面的受害人。一方面是生命、身体、健康法益遭受侵害的直接受害人。直接受害人的主体资格并无特别要求,但须达到一定的损害程度,才能成立第三人惊吓损害。直接受害人的死亡和重伤属于严重的事故,近亲属对这种事故的心理反应强度较大,容易导致惊吓损害。但如果直接受害人仅发生轻微的皮肉之伤或胳膊骨折等,则不足以成立第三人惊吓损害。[64]即使第三人因此发生惊吓损害,也被认为是反应过度,而不被赋予损害赔偿请求权。
就直接受害人还有一颇值讨论的问题,即由单纯的危险所引起的第三人惊吓应如何处理。有时加害人的行为并未造成直接受害人的人身伤害,只是制造了某种危险,但足以导致第三人受惊吓。例如,一辆卡车从倒在地下的小孩身上开过,但幸好车辆未碾过他,也未发生伤害。然而站在一旁的母亲,目睹此刻,因突然受刺激而导致健康损害。反对者指出,单纯的危险导致惊吓损害不属于第823条第1款的保护目的范围,受害人应自己承担风险。[65]但通说认为,即使事故危险最终未发生,如足以构成第三人惊吓损害,也应予以赔偿。[66]
另一方面,就惊吓事故受损害的第三人而言,一般须与直接受害人有感情上或生存上的联系,其对直接受害人幸福安康的关心犹如对自身一般。[67]据此,第三人原则上须为直接受害人的近亲属。但也可广义理解为包括订婚者或未婚的生活伴侣。甚至有时在个案中还可以包括恋人。[68]但不包括邻居或远亲。[69]此外,法院判例还认可因母亲受惊吓而导致早产的胎儿,也属于第三人范畴。[70]
3.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一):等值性理论
按德国侵权法原理,对因果关系须进行双重的检验:其一,加害人的行为引起了特定的法益侵害后果,即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haftungsbegriindende Kausalitat),它属于责任成立的构成要件;其二,法益侵害导致某些具体损害发生,即责任范围的原因关系,它能够确定法益侵害与具体损害之间的联系。[71]我们先讨论前者。
判断加害人的行为与第三人惊吓损害之间是否存在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适用一般的因果学说原理。于此首先涉及的是等值性理论(aquivalenztheorie)。按该理论,原因就是对侵害结果的发生不能被排除考虑的条件。[72]因为任何导致后果发生的条件都不能被排除掉,它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故称为“等值”。[73]等值性因果关系的认定通常采用“若无,则不”(but-for)的检验公式,即无此条件,则无彼结果。
“若无,则不”的检验法则对于第三人惊吓损害的特殊性在于:不同于一般物理的、有形的人身侵害,第三人的健康损害是通过心理原因而间接引起的,然而,导致心理作用发生的行为事实不可通过重复事件的方式进行检验,因而不能确切地说明究竟何种情事对于损害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74]对此首先须明确,如果损害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不妨碍认定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75]例如,A女士目睹自己的宠物狗被B女士之大狗咬伤,从而发生惊吓损害,B对A之健康损害的侵权责任因果关系成立。[76]换言之,与物理性的人身伤害情形没有任何区别,第三人的心理反应引起的健康损害也可成立条件因果关系。[77]
从过滤侵权责任的意义上来说,等值性理论排除了那些与后果无关的行为。[78]例如,德国联邦法院1984年1月31日判决:原告某女士的丈夫因车祸死亡,她之前已曾酗酒,但随着丈夫去世更加深了其对酒精的依赖,因而请求被告就其健康损害进行赔偿。联邦法院认为,按生活经验可推断,即使没有其丈夫的死亡,原告的酒精依赖也会逐渐加重。因此,法院否定了在事故与原告健康损害之间的责任成立因果关系。[79]易言之,即使没有加害人致使其丈夫死亡,第三人的健康损害仍会发生,则该行为不应被视为原因。
4.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二):从相当性理论到法规保护目的
根据等值性理论所界定的条件与后果之间的联系,近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过于宽泛,侵权责任可能由于因果链的无穷无尽而漫无边际。因此,用等值性理论限定第三人惊吓损害的责任成立,仅具有较小的作用;在等值性理论的基础上需要以相当性理论(Adaquanztheorie)和法规目的说(Normzweck)进一步对因果关系和责任成立进行限定。
相当性理论有两种表述方式,从积极角度说,它表明行为引起后果具有高度可能性(erhahte Maglichkeit);从消极角度说,后果发生的极低可能性可以作为排除因果关系的理由。据此,按事物的发展进程通常不会发生损害后果的,就不具有因果性,也不可归责于行为人。[80]可见,相当因果关系的本质需要一种高度盖然性判断(Wahrscheinlichkeit-surteil)[81]但究竟这种盖然性判断的标准为何,存在争议。首先,它不取决于加害人的主观预测能力,而必须以客观的可预见性(objektiver Vorhersehbarkeit)作为判断标准。其次,德国民法通说认为,应以在损害事件发生时的一个“最优观察者”(optimale Beobachter)作为标准。换言之,如果行为所引发的后果是作为一个最优观察者所能够预见的,则因果关系成立。[82]但所谓理想的观察者近乎全知,他总是可以预知事物发展的进程,因此难以形成对因果联系的有效限制,甚至接近于等值性理论所界定的宽泛因果联系范围。[83]
德国学说和判例中通常都会肯定,加害人导致直接受害人的重伤或死亡与第三人惊吓损害之间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因为根据最优观察者的判断,该后果具有高度盖然性,并“相当地”(adaquat)被引起。[84]德国联邦法院在1971年5月11日判决中也指出,某女士因获知其丈夫因事故死亡而遭受健康损害,“尽管比较少见,但这种结果无论如何对于加害人来说并非不可预见”,从而该损害是由“相当的原因”引起的。[85]
但对于实际发生的惊吓损害案件而言,相当因果关系很少起到限制侵权责任的作用。德国学者施密特提出讨论一件案件:一位父亲闻知其儿子因交通事故而致胳膊受伤,因激动而心脏病发作,并在数周之后去世,其继承人请求丧失扶养之损害赔偿。德累斯顿地方上诉法院否定本案中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因为加害人不可预见该损害后果。[86]但是,如从最优观察者的视角出发,惊吓的受害者存在心脏病,并且听闻儿子发生事故而激动,以致心脏病发作死亡,这些既非完全不可能,亦非超出日常生活经验之外,因此符合相当因果关系。就本案责任限制的实质理由而言,并非在于相当因果关系,而是基于其他的价值判断,即法院为避免惊吓损害责任的漫无边际。[87]但这种限制侵权责任成立的价值判断和理由,并不包含于因果关系理论之内。
为弥补相当性理论之不足,德国民法理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由拉贝尔、卡雷默尔等人发展出法规目的说,进一步作为损害赔偿责任的限制措施。[88]法规目的说的基础思想是:每一个义务或法律规范都包含特定的利益范围,行为人只应为侵害这种保护范围内的利益而负担责任,因此,责任的成立要件必须是损害处于被保护的利益范围之内。[89]简言之,当一项损害的种类和产生方式处于责任成立的法律规范或契约义务的保护目的或保护范围之内时,才能构成损害赔偿责任。[90]一般认为,法规目的说是相当因果关系说的补充,二者可并列运用。相当性之判断,是以一种经验认识为基础,并基于一般人对损害后果的可预见性;而法规保护目的则是立法者为阻止特定损害发生而确立的一项规范。通常考察侵权责任构成,首先应检验损害与侵害行为是否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其次确定损害是否处于法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后者会在前者基础上进一步对责任成立进行限制。[91]易言之,损害之发生虽具相当因果关系,但在法规目的之外者,仍不得请求损害赔偿。[92]据此,《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所提及的绝对性法益也存在着受保护的界限。这些保护界限,或由某些具体的法益保护规定指示出来,或在裁判中由法官予以具体化。[93]
就第三人惊吓损害而言,前文所提及的德国联邦法院1971年5月11日判决书的裁判理由即被认为是法规目的说的代表。[94]该判决指出:第三人所受惊吓不仅要达到医学上认为的健康损害,而且当事人所受影响须超出听闻或经历严重事故时通常的反应程度,“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保护目的仅仅涵盖,按其性质和严重性超出这种程度的健康损害。”继而法院指出,按“常人观念”,既非疾病、亦非与责任有关的健康损害,处于行为规范的保护范围之外,从而将一般的精神痛苦、忧伤等排除在损害赔偿责任之外。[95]德国联邦法院1989年4月4日判决再次援引以上裁判理由指出:根据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保护目的,只在第三人的健康损害状况超出了近亲属在这种情事下的一般损害程度时,才存在赔偿请求权。[96]
作为一种责任限制措施,规范目的说不仅界定了惊吓损害的程度,而且也限定了请求权人的范围。如果第三人与直接受害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第三人即使遭受程度严重的健康损害,也不属于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之保护范围,而仅仅是一般生活风险。例如,听闻某政治家被杀害或遭遇某种灾难事故而受精神打击。[97]此外,按法规目的说,第三人因近亲属死亡所发生的财产损失也被排除在责任范围以外。例如,一对夫妇已经花钱预订一项旅游活动,后因儿子死亡而取消旅游,因此向加害人主张该笔旅游费用的损失。尽管该财产损失与加害人行为之间成立条件因果关系,但因缺少法律保护目的,因而法院判决驳回。[98]
除以上各种理论之外,尚须明确,受害人的体质特别脆弱、容易发生身体或心理损害,是否影响因果关系的成立呢?例如,受害人的内心特别敏感,或原本已患心脏病,如遭受惊吓事故,轻易便发生健康损害。德国民法学理和实务向来认为,加害人的必须容忍受害人的具体特性,不得以受害人的容易受伤体质作为抗辩事由。[99]实践中有时称之为损害赔偿法的“全有或全无原则。”[100]事实上,受害人的特殊体质既不影响条件因果关系,也不影响相当因果关系的成立,因为如果没有侵害行为,则不会发生受害人的健康损害;而且,最优观察者也应该注意到受害人因可能具有身体或心理的缺陷而容易发生损害后果。但是,如果对直接受害人的加害行为完全微不足道,且并非基于受害人的特殊体质而发生损害,那么当事人的心理反应与其诱因就非常不成比例,从而缺少显著性而不构成侵权责任。[101]
(二)第三人惊吓损害的违法性
违法性是侵权责任第二层次的检验要件。德国民法学说上区分结果不法和行为不法。前者是指某种行为导致一项第823条第1款意义上绝对性法益的损害结果,如果没有合法的抗辩事由,该结果即指示其行为违法性。[102]后者是指在不作为和间接侵权行为情形下,行为违背法秩序规定的特别行为规范或违反为避免损害而通常客观上应尽必要之注意义务,因而具有违法性。[103]行为不法说尤适用于违反交往义务( Verkehrspflicht)的不作为侵权行为。[104]
判断惊吓损害中的违法性,除了依据以上一般准则之外,还可通过规范的保护目的来判定行为的违法性。[105]施密特建议按具体情形分别认定惊吓侵权行为的违法性:(1)对于“直接惊吓损害”,因为受害人之身体或健康发生损害,侵害行为总是具有违法性;(2)对于“作为法益损害后果的惊吓损害”,取决于惊吓损害是否为规范保护范围所包括,例如,侵害车辆导致受害人血压升高或急性循环障碍,虽然可能发生,但并非十分显著,因而不具有违法性;因长期剥夺某人自由而致严重的精神障碍,可认定为显著的违法侵害;(3)第三人惊吓损害须进行具体化评价。例如,第三人因陌生人受侵害所生惊吓损害,不具有违法性,属于一般生活风险;救援事故的第三人发生惊吓损害,也不具有违法性;与直接受害人有密切联系的近亲属,因受惊吓而发生健康损害,由该损害后果指示出行为的违法性。[106]
(三)第三人惊吓损害的有责性
第三人惊吓损害采过错责任原则,须检验侵权人的责任能力和过错形式(故意和过失)。此处仅讨论后者。行为人针对惊吓受害人故意实施侵害行为,不论是直接惊吓,还是第三人惊吓,都必须承担责任。[107]就过失而言,惊吓侵权行为也无特异之处。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76条第2款,过失是指“未尽交往中必要之注意”,具体含义是行为人对损害后果的应预见和能避免,如其未预见且未避免,即存在过失。[108]此处行为人应尽注意的标准并非取决于个人能力,而是按其所属人群的成员平均水平来确定。据此,侵害直接受害人并致其伤亡,导致第三人受惊吓而发生健康损害,通常应为加害人所预见的。[109]如其未预见或未避免,行为人对第三人之损害则存有过失。
(四)第三人惊吓侵权的损害赔偿
倘若经过上述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检验,加害人的行为成立侵权责任,继而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损害的种类、范围及原因、规范保护目的等因素。[110]
1.损害的范围及精神痛苦金
侵权行为导致第三人受惊吓而侵害其健康,将发生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首先,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主要是治疗(尤其是心理治疗)所发生的医疗费用,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收入损失等。[111]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49条,受害人得请求恢复原状,或请求支付恢复原状所需之必要金额。据此,惊吓受害人因健康损害得请求加害人送医救治或支付相应的金钱。
关于非财产损害赔偿,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53条第2款规定,侵害他人身体、健康、自由、性自主,须赔偿受害人精神痛苦金。在第三人惊吓损害情形,须澄清的是,受害人并非因亲近之人死亡或重伤发生悲痛、忧伤便可获得赔偿,而是受害人超出一般的悲痛、发生自身健康损害,才可请求(侵害健康的)痛苦金赔偿。[112]
精神痛苦金主要有补偿功能和抚慰功能,受害人所遭受身体和心理的痛苦应予赔偿,心灵应得到慰籍。[113]在第三人惊吓损害情形中,受害人之健康损害固然产生精神痛苦,但事实上,第三人因目睹或听闻近亲属的死亡和重伤所带来的悲痛、忧伤等不良情绪才是精神痛苦的最重要根源。然而,现行德国民法对没有权利侵害作为请求权基础的、单纯的“丧亲之痛”却明确不予赔偿,因此道奇希望通过第三人惊吓损害的痛苦金赔偿,部分地达到赔偿近亲属“丧亲之痛”的目的。[114]但因为这种观点与立法目的不符,通说还是拒绝将其视作纯粹精神痛苦的替代赔偿形式。[115]
就第三人惊吓损害的痛苦金赔偿数额来说,德国司法实务认定其比一般的身体伤害痛苦金要少,在1990年之前,通常在1000-5000马克之间,近年来达到9000-20000欧元,并呈逐渐上升趋势。[116]此外,直接受害人在死亡之前发生的痛苦金请求权可以继承,其与第三人惊吓损害的痛苦金请求权并不相互排斥。[117]
2.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
与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类似,认定法益侵害与具体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联系(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也须以等值性、相当性和法规目的说作为判断标准。[118]就第三人惊吓损害而言,须说明者有三。
第一,按等值性理论,受害人之健康受侵害与具体所受财产损失和非财产损失之间存在条件关系,若无加害人侵害受害人之健康,则不会发生具体损害结果。
第二,按相当性理论,从“最优观察者”或“有经验的判断者”来看,通常可以预见侵害健康会导致损害后果的发生,相当因果关系成立。换言之,如果损害后果并非处于盖然性之外,加害人即须对其负责。[119]而且,德国司法实践中,也不要求加害人对具体的损害范围有预见。[120]
第三,在以上基础上,损害范围须进一步受法规保护目的的限制。[121]
3.过错相抵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254条,如果受害人的过错对损害发生有共同作用,则损害赔偿义务及赔偿范围将根据双方过错程度进行分摊,受害人之请求权将予以缩减。过错相抵体现了法律平等对待加害人和受害人的思想,即受害人同样也须为自己的过错负责。[122]在第三人惊吓损害案型中,如受害人(即惊吓的第三人)本身有过错当然适用过错相抵。但有疑问的是,受害人是否须为直接受害人之过错负责。对此,德国民法理论和实务通说持肯定态度,但其论证理由和法律依据却存在争议。
帝国法院(RG)曾经类推《德国民法典》第846条,认为间接受害人应承担死亡的直接受害人的过错后果。[123]但根据第846条规定,近亲属死亡的间接受害人仅在第844条、第845条规定的丧葬费、抚养费和劳务损失的项目上,须为直接受害人的过错负责。正如上文所述,受惊吓的第三人并非第 844条、第845条意义上的间接受害人,恰恰是第823条第1款意义上的直接受害人,不属于第846条的规范对象。因此,德国联邦法院放弃帝国法院的观点,并评论道:
与第844条、第845条之情形有别,在第三人惊吓损害,受害的第三人第823条第1款的法益受到侵害,由此成为享有独立请求权的直接受害人。第844条、第845条所产生间接受害人请求权的前提是一个指向直接受害人的、并成立损害或责任的影响(Einwirkung) 。……第844条、第845条框架下有意义的规整并不适用于第三人由第823条第1款所生之独立的请求权。对于该项请求权无关紧要的是:这是由侵害他人而媒介造成第三人的直接损害。[124]
根据现今德国民法理论和实务通说,惊吓损害的第三人就直接受害人的过错应适用民法典第254条的过错相抵。[125]但根据第254条第1款,不能立即得出受害人应对第三人(惊吓损害中的直接受害人)的过错负责的结论。即使第254条第2款第二句规定过错相抵“准用第278条之规定”,也只表明受害人须对法定代理人、债务履行辅助人的过错负责。虽然德国民法学说和实务将受害人为第三人的过错负责的情形,扩张至不具有债务关系的其他类型第三人,例如事务辅助人、共有人等,[126]但仍不能说明惊吓损害的受害人为何须对第三人的过错负责。对此,判例和学说的论证理由有二:其一,惊吓侵权中的受害人与直接受害人之间具有人身方面的紧密联系,这构成第三人惊吓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因此,该请求权应与直接受害人的过错发生联系;其二,倘若不允许惊吓第三人因直接受害人的过错而缩减其请求权,则加害人必须先对第三人全额赔偿,然后(按连带债务)向直接受害人或其遗产进行追偿。如此则意味着,直接受害人负有义务照顾自己,以免自己死亡或重伤而致近亲属受到惊吓损害,但这种义务将限制个人的自主决定。尤其在直接受害人自杀的情形下,责任将全部归于他,其结果将更显不合理。因此,应准用第254条之规定,直接缩减第三人对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127]
但罗谢尔德斯却不赞同准用第254条。他认为,第844条、第845条的近亲属损害和第三人惊吓损害,都是由直接受害人之死亡或受伤而间接引发的。从形式上说,即使直接受害人对加害人不享有请求权,但惊吓的第三人仍有可能对其享有请求权。但是,从价值判断来看,这种结果不能令人接受,因为这两项请求权在法律上具有紧密联系。也即,只有直接受害人的伤亡必须可归责于加害人,那么,近亲属的惊吓损害也才可归责于同一加害人。反之,如直接受害人的伤亡不可归责于加害人,同样地,惊吓损害第三人也不享有请求权,因为此时加害人的行为与第三人损害在责任法上没有联系。总之,对直接受害人死伤的可归责性,同样适用于惊吓损害第三人的请求权。因此,应根据第846条,认定惊吓损害第三人为直接受害人的过错负责。[128]罗氏的观点完全混淆了第三人的请求权究竟是因死亡而发生,还是因死亡的惊吓而发生。前者是因死亡这一事实本身而产生,死者本身对死亡的发生有过错,第三人的请求权当然须就该过错进行缩减;后者是第三人因自身受害而产生的请求权,本来就不该考虑是否因他人(死者)的过错而缩减。[129]因此,德国民法学理和实务努力论证的恰是在后者情形下,第三人请求权为何也适用死者的过错相抵。
哈格尔从另一个角度对通说提出批评。他指出,现行法并不认可将惊吓受害人与直接受害人的情感上的联系作为过错相抵的归责标准。倘若直接受害人也有过错,那么,他与加害人本应对第三人承担连带之债。[130]但毕竟直接受害人的过错原因会影响第三人的请求权,因此,在连带之债的外部关系中,应缩减第三人对加害人的请求权,可称为“受干扰的连带之债”(gestrate Gesamtschuld)。[131]但如果近亲属之间存在法律上的责任优待,则结果更为复杂。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359条、第1664条规定,在夫妻之间、父母对子女只须尽到如同处理自己事务的注意义务即可,换言之,如果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则不负责任。[132]将此原则适用于第三人惊吓损害,如果直接受害人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为保护家庭关系,即使在连带之债的内部关系中加害人也不能向直接受害人追偿,在连带之债外部关系中也不应缩减第三人的请求权。[133]由以上可以推论,如果直接受害人对第三人不存在责任优待(例如同居伴侣或陌生人之间),则第三人之请求权因前者的过错应予缩减;如果存在责任优待,但直接受害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第三人请求权也相应缩减;如果存在责任优待,且直接受害人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则不应缩减第三人之请求权。比较而言,哈格尔的考虑更为周全。
第三人惊吓损害除了可适用过错相抵之外,德国司法实务还认可,受害人自身容易受惊吓损害的特殊体质,虽然不影响惊吓损害的责任成立,但可作为缩减加害人财产损害赔偿和痛苦金损害赔偿的事由。[134]
三、我国民法上第三人惊吓损害的请求权基础
基于德国第三人惊吓损害理论与实务的考察,对比我国民事立法和学说,可以明确我国第三人因近亲属死伤而请求损害赔偿的项目类型,并可准确地界定相应的请求权基础。
(一)第三人的惊吓损害赔偿请求权与间接损害赔偿请求权
可以明确的是,第三人惊吓损害赔偿请求权在《德国民法典》中构成第823条第1款意义上的独立请求权,与第844条、第845条间接损害赔偿请求权有本质区别。我国法律对于第三人的间接损害赔偿请求权有明文规定,[135]但对于“林玉暖案”则似乎欠缺可资适用的法律规定。然而,正如德国民法所表明的那样,第三人惊吓损害其实构成一项独立的侵权行为,应适用侵权行为法的一般条款,即《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或《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6条与第三人的间接损害赔偿请求权有别。在此方面,杨立新教授将因丧失扶养来源的间接损害赔偿请求权人与惊吓损害的请求权人归入一类,统称为间接被侵权人的观点,[136]实乃将本质上不同的事物混为一谈,其认识上的错误根源恐在于对第三人惊吓损害的构成要件认识不清。
为表明第三人惊吓损害在我国民法上亦可建立在侵权行为一般条款的基础上,笔者尝试运用德国民法关于第三人惊吓损害赔偿的责任成立和责任范围的教义学,来解决“林玉暖案”中受害人的请求权。
首先,从该当性来看,林玉暖因目睹儿子受伤而当场休克并被送医救治,从而发生健康损害,且与直接受害人有密切的亲属关系。在加害人行为与林玉暖的健康损害之间,均符合等值性和相当性因果关系,且属于《民法通则》第 106条第2款、《侵权责任法》第2条、第6条的保护目的范围。
其次,从违法性而言,加害人的行为侵害了林玉暖的健康权,该权利受侵害本身即指示行为的违法性。
最后,从有责性而言,加害人虽然不是故意通过侵害直接受害人而令林玉暖健康权受损,但已违反社会上通常行为人的注意义务,因而主观上具有过失。在考察加害人的责任成立后,进一步确定林玉暖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范围,包括住院医疗费等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但由于林玉暖自身患有疾病,属于易受伤害体质,虽不影响侵权责任成立,但应根据其对损害后果的作用大小,相应地扣减损害赔偿数额。因此,法院判决被告承担20%的财产损害赔偿(《侵权责任法》第16条、第20条,《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7条第1款),并酌定精神抚慰金2000元(《侵权责任法》第22条、《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8条第1款、《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条)的结论应值赞同。由于该案发生在《侵权责任法》颁布实施之前,故而法院最终以《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作为裁判依据,也说明侵权行为法的一般条款可以作为原告的请求权基础。
(二)第三人的惊吓损害赔偿请求权与“丧亲之痛”
《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有意未规定第三人对近亲属死亡“丧亲之痛”的精神损害赔偿,而且第三人继承直接受害人的精神痛苦金请求权也极受限制,这构成了德国侵权法最重大的缺陷之一。在当下欧洲侵权法统一化进程中,其愈发显得不合时宜。因此,道奇在理论上寄望于第三人惊吓损害,期待它能够部分发挥赔偿“丧亲之痛”的功能。但这种观点犹如饮鸩止渴,更不可取。因为无论是欧陆还是英美,通常将第三人因近亲属死亡发生的精神损害赔偿,界定为非独立的、派生的请求权,而第三人惊吓损害则为第三人自身的、独立的请求权。因此,德国民法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直接承认第三人丧亲之痛的精神痛苦金请求权(以一般人格权作为请求权基础),而不是将二者互相替代。
我国历来认可第三人因丧亲之痛的精神损害赔偿,[137]从而与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模式相同,不至于发生德国法上的理论压力。但是,笔者的另一层担心是,“林玉暖案”客观上(好不容易)独立出来的第三人惊吓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可再与第三人非独立的、派生请求权归人同一类。然而“林玉暖案”的承办法官却在案例评析中将二者混淆,其指出:本案虽无法律规定,但《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规定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与本案中直接受害人受到伤害有相似之处,因为二者均为三角关系、皆为第三人受到损害,且与直接受害人存在特殊关系。因此扩张解释该条规定,使第三人享有对加害人的赔偿请求权。[138]其推理过程可总结为:法律规定第三人因近亲属死亡得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类似地,也可因近亲属受伤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针对此种观点,须澄清者有二。其一,《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就死者近亲属的精神损害(丧亲之痛)作出规定,根据立法目的,该司法解释的起草者认为近亲属不可因直接受害人受伤而提出精神损害赔偿。[139]因此,直接受害人受伤时,近亲属不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并非法律上的漏洞,而是立法者“有意义的沉默”,[140]故而不存在类推《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的前提。其二,即使承认法院的“扩张解释”成立,间接受害人得请求因直接受害人受伤而发生的精神损害赔偿,但仍不可以此作为第三人惊吓损害的请求权基础。因为前者属于间接受害人就直接受害人受人身伤害的派生请求权,而后者属于第三人因惊吓所产生的独立请求权。总之,“林玉暖案”的裁判者有善意的愿望,赋予第三人惊吓损害的赔偿请求权,但欠缺明晰的概念体系和法律理由,因而即使其裁判结果合理,但其论证理由存在瑕疵,需要善加厘清。
兹就我国民法有关第三人就近亲属的死亡或受伤(包括惊吓损害)的各项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图示方式明确各自请求权基础如下:
【注释】
[1]Larenz/Canaris,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H.,BT, 2. Halbband, 13. Aufl.,Munchen, 1994, S.350.
[2]王泽鉴教授指出:对第三人惊吓损害“绝对予以肯定,难免增重加害人之负担,而全部加以否定,对受损害之人则殊不利。”参见王泽鉴:《第三人与有过失》,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3]关于欧洲各国的第三人惊吓损害的法制概况,参见[德]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张新宝校,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87 -96页。有关英美法的状况,参见潘维大:《第三人精神上损害之研究》,载《烟台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张新宝、高燕竹:《英美法上“精神打击”损害赔偿制度及其借鉴》,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5期。
[4]Claus-Wilhelm Canaria, Systemdenken und Systembegriff in der Jurisprudenz, Belin,1969, S. 45.
[5]Claus - Wilhelm Canaria, Systemdenken und Systembegriff in der Jurisprudenz,S. 81ff.
[6][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3,163页。
[7]Larenz,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and I, AT, 14. Autl.,Munchen, 1987, S. 459. Munchener Kommentar zum Burgerlichen Gesetzbuch, 5. Aufl.,C. H. Beck, Munchen, MunchKomm BGB/Oetker, § 249, Rn. 268.
[8]MttnchKomm BGB/Wagner,§844, Rn.1.
[9]Staudingers Kommentar zu Bttrgerlichen Gesetzbuch, Berlin, Staudinger/Rgthel (2007),§ 944, Rn. 3.
[10]Fraenkel, Tatbestand und Zurechnung bei § 823Abs. 1 BGB, 1979, S. 164f. such vgl. MttnchKomm BGB/Wagner,§823,Rn. 80.
[11]MunchKomm BGB/Wagner,§823,Rn. 80. Staudinger/Schiemann (2005),§ 249,Rn. 44.
[12]Larenz, Schuldrechts, AT, 5.460. Brutggemeier, Deliktarecht, Baden, 1986, S. 138.
[13]Staudinger/Hager (1999),§823,Rn. B34. Brand, Schadensersatzrecht, Munchen, 2010, S. 35.
[14]RGZ 133,270. in B. S. Markesini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to the German Law of Tor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0,pp. 103-104.
[15]BGHZ 56, 163=NJW 1971.1883.
[16]R.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aden nach § 8231 BGB als Promblem der wertenden Nonnkonkretisierung,Diss, 1991, S. 37在此意义上,王泽鉴教授在惊吓损害案件中,将两个受害人称为“前受害人”与“后受害人”,而不称为直接受害人或间接受害人,的确精准。参见王泽鉴:《第三人与有过失》,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17]R. 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aden, S. 20f
[18]MunchKomm BGB/Wagner,§823, Rn. 73. Staudinger/Hager (1999 ),§ 823, Rn. B20.
[19]Bruggemeier, Deliktsrecht, S. 136f. Deutsch/Ahrens, Deliktsrecht, 5. Auflage, Carl Heymanns Verlage, 2009, Rn.243.
[20]BGHZ 56, 163 = NJW 1971,1883.
[21]R.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 den, S.22.
[22]惊吓损害也可能表现为身体损害,即心理原因导致身体完整性受损,例如心脏病、循环系统障碍、震顫性麻痹等。这些损害是对身体的生命进程的干扰,因而可被视作第823条第1款意义上的健康损害。参见R. 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aden, S.35。
[23]MunchKomm BGB/Wagner, § 823, Rn. 80. Park, Grund und Umfang der Haftung fur Schockschaden, S. 128ff.
[24]Bruggemeier, Dehktsrecht, S. 137. Stahr, Psychische Gesundheitsschgden und Regress, NZV 2009,161.
[25]R. 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aden, S. 133ff.
[26]R. 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aden, S. 141.
[27]R. 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aden, S. 142ff.
[28]Stahr, Psychische Gesundheitsschaden und Regress, NZV 2009, 161.
[29]BGH NJW 1996, 2425. Staudinger/Hager (1999),§ 823, Rn. B29.
[30]R. 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aden, S. 146ff. Staudinger/Hager (1999),§823,Rn. B29.
[31]Staudinger/Schiemann (2004),§ 249,Rn. 43ff. Brtiggemeier, Deliktsrecht, S. 138. Larenz/Canaris, Schuldrechts,BT, 2. Halbband, S. 380ff.
[32]MunchKomm BGB/Wagner,§823, Rn. 81. Staudinger/Hager (1999 ),§823, Rn. B32ff.
[33]此处仅描述其基本要件,下文将予以详细讨论。
[34]Palandt Burgerliches Gesetzbuch Kommentar, C. H. Beck, Munchen, 2011,Palandt/Gruneberg, Vorbem. § 249,Rn. 40. Staudinger/Hager(1999),§823,Rn. B36. Brand, Schadensersatzrecht, S. 35.
[35]Palandt/Gruneberg, Vorbem. § 249, Rn. 40. Brand, Schadensersatzrecht, S. 35.
[36]Staudinger/Hager(1999),§ 823,Rn. B34.
[37]Larenz/Canaris, Schuldrechts, BT, 2. Halbband, S. 382L
[38]德国民法理论和实务中用“纯粹的精神痛苦”(bloae seelische Leiden/bloae Trauer/reine seeliche Schmerz)指称第三人不以法益侵害为基础的精神损害。Vgl. A. Schramm, Haftung fur Tatung: Eine 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 des englis-chen, franzttsischen und deutschen Rechts zur Fort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Haftungsrechts in Tatungsfallen, Mohr Siebeck,2010, S. 149. Huber, Kein Angeharigenschmerzensgeld de lege late-Deutschland auch kunftig der letzte Mohikaner in Europa o-der ein Befreiung aus der Isolation, NZV 2012, 5. OLG Nurnberg NZV 1996, 367.
[39]Erman/Ebert, BGB, 12. Aufl.,Vor§§249-253,Rn. 55.
[40]MunchKomm BGB/Wagner, § 844, Rn. 4. Staudinger/Rathel (2007),§844, Rn.15.
[41]Greger, Stellungnahme zum Entwurf eines Zweiten Gesetzes zur anderung schadensersatzrechtlicher Vorschriften, NZV 2002, 222. Klinger, Schmerzensgeld fur Hinterbliebene von Verkehrsopferna NZV 2005,290. Huber, NZV 2012, 5.
[42]Staudinger/Rathel (2007),§ 844, Rn.12.
[43]死者痛苦金请求权的依据在于,行将去世的人对死亡的恐惧和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有限。(Vgl. Deutsch/Ahr-ens, Deliktsrecht, Rn. 689, Rn. 710.)此外,痛苦金还取决于死者生前被病痛折磨的程度和时间。Katz/Wagner, Delik-tsrecht, 10. Auflage, Munchen, 2006, S. 293. OLG Kaln, VersR 2003,602.
[44]Deutsch/Ahrens, Deliktsrecht, Rn. 689, Rn. 701. MunchKomm BGB/Oetker,§253,Rn. 65.
[45]Katz/Wagner, Deliktsrecht, S. 293.德国联邦法院的一项判决指出,侵害事故直接导致死亡,(即未产生身体、健康的侵害),则不发生精神痛苦金请求权。BGH, NJW 1976, 1147.
[46]Huber, NZV 2012, 5.
[47]Deutsch/Ahrens, Deliktsrecht, Rn. 689, Rn. 694, Rn. 711.
[48]Huber, NZV 2012, 5.
[49]OGH, NZV 2002, 26. Klinger, NZV 2005, 290.
[50]Klinger, NZV 2005,290.auch vgl.Huber, NZV 2012, 5.
[51]在德国民法上,分析损害赔偿责任问题,首先须考虑责任是否成立,然后再审查责任范围。Fikentscher/Heine-mann, Schuldrecht, 10. Aufl.,Berlin, 2006, Rn. 581 f.
[52]Deutsch/Ahrens, Deliktsrecht, Rn. 12ff.侵权责任成立的三阶段论源自德国刑法理论,适用于《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侵犯法益、第1款违反保护他人法律的侵权行为类型。但不适用于第826条之故意悖于善良风俗的侵权行为。参见Larenz/Canaris, Schuldrechts, BT, 2. Halbband, S. 350。
[53]larenz/Canaris, Schuldrechts, BT, 2. Halbband, S. 370. Staudinger/Hager (1999),§ 823,Rn. Alff.
[54]Kuppersbusch, Ersatzanspruche bei Personenschaden, Munchen, 2006,S. 5. Larenz/Canaris, Schuldrechts, BT, 2.Halbband, S. 378. Staudinger/Hager (1999),§823, Rn. B26ff. Erman/Schiemann, BGB, 12. Aufl.,§823,Rn. 19.
[55]Schramm, Haftung fur Tatung, S. 149. Staudinger/Hager (1999),§823,Rn. B32.
[56]MunchKomm BGB/Wagner,§823,Rn. 80. Staudinger/Hager(1999),§823, Rn.B32.
[57]德文“allgemeine Verkehrsauffassung”直译为“一般交往观念”,根据英国学者Markesinis的译文,笔者翻译为“常人(the man in the street)观念”。See Markesinis,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to the German Law of Torts, p.%。
[58]BGHZ 56, 163=NJW 1971,1883. such Vgl. BGH NJW, 1984,1405.
[59]德国联邦法院一贯坚持上述标准。例如1989年4月4日判决理由指出:“因心理原因发生损害赔偿义务,仅在如下情形被肯定:即心理病理学上的严重后果持续一段时间,且该后果显然超出了因令人悲痛的事件而发生的、对于一般健康状况而言并非轻微的影响,因而按照一般交往观念也被看作是身体或健康损害。”参见BGH NJW, 1989, 2317。
[60]MunchKomm BGB/Oetker,§249, Rn. 145.
[61]BGHZ 56, 163 =NJW 1971. Larenz/Canaris, Schuldrechts, BT, 2. Halbband, S.382.
[62]R. 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aden, S. 31 ff.
[63]MunchKomm BGB/Wagner,§823, Rn.82. Schramm, Haftung fur Tatung, S.153.
[64]Staudinger/Hager(1999),§ 823, Rn. B36.
[65]R. 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aden, S. 177.
[66]Staudinger/Hager (1999),§823,Rn. B36. MunchKomm BGB/Oetker, § 249, Rn. 148.
[67]R. 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aden, S. 173.
[68]MunchKomm BGB/Oetker, § 249,Rn. 147. Schramm, Haftung fur Tatung, S. 156.
[69]R. 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aden, S. 174f.
[70]BGH NJW 1985,1391. Palandt/Grtineberg, Vorbem. § 249, Rn. 40. Deutsch/Ahrens, Deliktsrecht, Rn. 695.近来德国民法文献中经常论及与直接受害人完全不相干的第三人,因见证事故现场而遭受惊吓损害,也可请求损害赔偿。参见Larenz/Canaris, Schuldrechts, BT, 2. Halbband, S. 381. MunchKomm BGB/Oetker,§249,Rn.147 。
[71]Looschelders, Schuldrecht, AT, 7. Aufl.,Kaln Munchen, 2008,Rn.890. Deutsch/Ahrens, Deliktsrecht, Rn. 46ff.
[72]Brox/Walker, Allgemeines Schuldrecht, 35. Aufl.,Munchen, 2011,§30, Rn. 2.
[73]Fikentscher/Heinemann, Schuldrecht, Rn.621. Palandt/Gruneberg, Vorbem.§249,Rn. 25. Erman/Ebert, BGB,12. Aufl.,Vor§§249-253, Rn. 30.
[74]R. 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aden, S.44.
[75]MunchKomm BGB/Oetker,§249, Rn. 143ff. Staudinger/Schiemann(2005),§249, Rn.39ff. BGHZ 56, 163=NJW 1971,1883.
[76]Larenz, Schuldrechts, AT, S.433.
[77]R. 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aden, S. 99.
[78]Fuchs, Deliktsrecht, 7. Aufl.,Berlin, Heidelberg, 2009, S.71;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页。
[79]BGH NJW 1984, 1405.该案虽非典型的“惊吓”损害,但也是第三人因近亲属死亡而发生健康损害,故德国民法文献中,常将该案置于第三人惊吓损害中讨论。Staudinger/Hager (1999),§823, Rn. B32.
[80]Deutsch/Ahrens, Deliktsrecht, Rn. 52. MtinchKomm BGB/Oetker,§249, Rn. 105.
[81]Medicus/Lorenz, Schuldrecht I, AT, 18. Aufl.,C. H. Beck, Munchen, 2008, 5.311. Brox/Walker, Allgemeines Schuldrecht, § 30, Rn. 8.
[82]MunchKomm BGB/Oetker,§249, Rn.106. Staudinger/Schiemann (2005),§249, Rn.15.
[83]Brox/Walker, Allgemeines Schuldrecht, § 30, Rn. 9. Larenz, Schuldrechts, AT, S. 437.尽管拉伦茨建议用“有经验的观察者”取代这种具有高度认知能力的“最优观察者”(Larenz, Schuldrechts, AT, S. 440.),但是否能对因果关系进行有效限制,仍值得怀疑。
[84]R. 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 den, S. 100. Dolff, ubungsklausur-Die schockierte Ehefrau, Jus 2009,1007.
[85]BGHZ 56, 163=NJW 1971,1883.
[86]OLG Dresden, HRR 1942, Nr. 276. zitiert aus R. 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atden, S. 63.
[87]R. 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aden, S. 63ff.
[88]Lang, Normzweck und Duty of Care, Munchen, 1983, S. 15ff. Caemmerer, Das Problem des Kausalzuammenhangs im Privatrecht Freiburg, 1956. Stoll, Kausalzusanunenhang und Normzweck im Deliktsrecht, Tubingen, 1968.
[89]Brox, Ailgemeines Schuldrecht, § 30, Rn. 12. Lnoschelders, Schuldrecht, AT, Rn. 907.
[90]Palandt/Gruneberg, Vorbem. § 249,Rn.29. Erman/Ebert, BGB, 12. Aufl.,Vor § §249-253,Rn. 34.
[91]Deutsch/Ahrens, Deliktsrecht, Rn. 56.但有时法规保护范围也会超出相当因果关系范围,例如《德国民法典》第848条规定,侵夺他人之物的行为人,对于偶然事件造成物之毁损灭失也须负责任。
[92]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93]Lang, Nonmzweck und Duty of Care, S. 138ff.
[94]Fuchs, Deliktsrecht, S.72f.
[95]BGHZ 56, 163=NJW 1971,1883. Lang, Normzweck und Duty of Care, 1983, S. 144.
[96]BGH NJW 1989, 2317.
[97]Fuchs, Deliktsrecht, S. 73. R. 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aden, S. 162L
[98]BGH NJW 1989, 2317. Larenz/Canaris, Schuldrechts, BT, 2. Halbband, S.383.
[99]Staudinger/Schiemann (2005),§ 249, Rn. 39. Kuppersbusch, Ersatzanspruche bei Personenschaden, S. 4. Stahr,Psychische Gesundheitsschaden und Regress; NZV 2009,161. Dahm, Die Behandlung von Schockschaden in der hachstrichterlichen Rechtspruchung, NZV 2008, 187. BGH NJW 1996, 2425.判例中经常提到:Wer einen gesundheitlich schon geschwachten Menschen verletzt, kann nicht verlangen, so gestellt zu werden, als wenn der Betroffene gesund gewesen ware。
[100]Heβ,Haftung un Zurechenung psychischer Folgenschaden, NZV 1998, 402. BGH VersR 1991,704=NZV 1991,386.
[101]BGH NJW 1996, 2425. BGH NJW 1998, 810. Staudinger/Hager(1999),§823,Rn. B29. Palandt/Gruneberg,Vorbem.§249,Rn.38.
[102]Deutsch/Ahrens, Deliktsrecht, Rn. 82. Staudinger/Hager(1999),§ 823, Rn. A3. MunchKomm BGB/Wagner,§823, Rn.7.
[103]Palandt/Sprau, § 823, Rn. 24. Peifer, Schuldrecht, gesetzliche Schuldverhgltnisse, 2. Aufl.,2010, S. 116.
[104]单纯的不作为并非一定具有违法性,因此需要查明为避免损害后果何种行为是必要的,以及不作为是否客观上违反7该义务。参见Peifer, Schuldrecht, S. 117. Larenz/Canaris, Schuldrechts, BT, 2. Halbband, S. 368f。
[105]R. 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gden, S. 101.
[106]R. 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aden, S. 192ff.
[107]R.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aden, S. 96.
[108]Larenz, Schuldrechts, AT, S.282. Looechelders, Schuldrecht, AT, Rn. 514.
[109]R. 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aden, S. 97. Dolff, Jus 2009,1007.
[110]Fuchs, Deliktsrecht, S. 86ff. Deutsch/Ahrens, Deliktsrecht, Rn. 19ff.
[111]MunchKomm BGB/Oetker, § 249,Rn. 106. Schramm, Haftung fur Tatung, S. 160. Stahr, NZV 2009, 161.
[112]Deutsch/Ahrens, Deliktsrecht, Rn. 695. R. Schmidt, Die Haftung fur Schockschaden, S. 185.
[113]Brand, Schadensersatzrecht, S. 88. Palandt/Gruneberg, § 253, Rn. 4.
[114]Deutsch/Ahrens, Deliktsrecht, Rn.711.类似观点亦可参见Staudinger/Schiemann (2005),§253, Rn.13。
[115]Larenz/Canaris, Schuldrechts, BT, 2. Halbband, S. 382f Staudinger/Hager (1999),§ 823,Rn. B34
[116]Schramm, Haftung fur Tatung, S. 160f.
[117]MunchKomm BGB/Oetker, § 249, Rn.144. Staudinger/Schiemann (2005),§249,Rn. 44. Schramm, Haftung fur Totung, S. 162.
[118]Peifer, Schuldrecht, S. 134.
[119]Deutsch/Ahrens, Deliktsrecht. Rn.615.
[120]Fuchs, Deliktsrecht, S. 86f.德国联邦法院指出:侵害他人之身体或健康,应对损害后果负责,而且不需要加害人对损害后果有所预见。参见RGH NJW 1996, 2425。
[121]Katz/Wagner, Deliktsrecht, S. 93. Deutsch/Ahrens, Deliktsrecht, Rn. 620.
[122]Looschelders, Die Mitverantwortlichkeit des Geschadigten im Privatrecht, Mohr Siebeck, 1999,S. 118ff.
[123] Staudinger/Hager (1999),§ 823, Rn. 1338. Caemmerer, Das Problem des Kausalzuammenhangs im Privatrecht, S.15.《德国民法典》第846条规定:“在第844条、第845条的情形下,第三人所遭受的损害发生时,受害人的过错共同起到作用的,第254条之规定适用于该第三人之请求权。”
[124]BGHZ 56, 163 =NJW 1971,1883.
[125]Larenz, Schuldrechts, AT, S. 548. MunchKomm BGB/Oetker, § 254, Rn.10. Patandt/Gruneberg, § 254, Rn. 56.
[126]Staudinger/Schiemann(2004),§ 254, Rn. 104fl. MunchKomm BGB/Oetker, § 254, Rn. 126ff. Palandt/Gruneberg,§254,Rn.49ff.
[127]BGHZ 56, 163 = NJW 1971,1883. Schramm, Haftung fur Totung, S. 161. Staudinger/Hager (1999),§ 823,Rn.B38. Deutsch, Haftungsrecht, Koln, Belin, Bonn, Munchen, 1976, S. 482.王泽鉴教授认为,第三人之权利系基于侵害行为整个要件而发生,因而不能不负担直接受害人之过失。参见王泽鉴:《第三人与有过失》,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3页。
[128]Looschelders, Die Mitverantwortlichkeit des Geschadigten im Privatrecht, S.541ff.
[129]英美法上彻底区分第三人因近亲属死亡而产生的派生请求权(derivative claim),例如丧葬费、抚养费等,以及因惊吓损害产生的独立请求权(independent claim),且只对前者适用死者的过错相抵。See Markesinis,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to the German Law of Torts, p. 103.
[130]瓦格纳指出,帝国法院的实践早已提示,加害人向第三人赔偿之后,根据第426条可向直接受害人追偿。参见RGZ 157, 11. MtlnchKomm BGB/Wagner,§823, Rn. 83 。
[131]Hager, Das Mitverschulden von Hilfspersonen und gesetzlichen Vertretern des Geschadigten, NJW 1989, 1640.Staudinger/Hager (1999),§823,Rn. B39.
[132]Brox/Walker, Allgemeines Schuldrecht,§20, Rn. 19. Eckert, Schuldrecht, AT, 4. Aufl.,Rn. 234.
[133]Staudinger/Hager (1999),§ 823, Rn. B39.
[134]Kuppersbusch, Ersatzanspruche bei Personensehaden, S. 6. OLG Hamm, NZV 1998, 413. Erman/Schiemann, BGB,12. Aufl.,§823, Rn. 20.
[135]根据《侵权责任法》第16条、《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条、第17条,近亲属得向加害人请求因直接受害人死亡而发生医疗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赔偿金,等等。
[136]杨立新:《侵权責任法》,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56页。
[137]参见《侵权责任法》第18条、第22条和《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等。
[138]《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06)思民初字第5968号民事判决“评析”》,载最高人民法院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第70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页。
[139]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59、60页。我国有学者建议,在受害人遭受严重伤害时,赋予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参见张新宝主编:《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52-255页),但此属理论建议,未获得立法承认。
[140][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49页。第三人对近亲属受伤时,可能发生财产损失,例如丧失扶养来源,但我国法律将该项目计人直接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之中。《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7条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第4条规定,原先的被扶养人生活费项目在《侵权责任法》实施后计人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中。另参见本期笔谈孙维飞的论文:《英美法上第三人精神受刺激案型的处理及其借鉴意义》。
- 认准易品期刊网
1、最快当天审稿 最快30天出刊
易品期刊网合作杂志社多达400家,独家内部绿色通道帮您快速发表(部分刊物可加急)! 合作期刊列表
2、100%推荐正刊 职称评审保证可用
易品期刊网所推荐刊物均为正刊,绝不推荐假刊、增刊、副刊。刊物可用于职称评审! 如何鉴别真伪期刊?
都是国家承认、正规、合法、双刊号期刊,中国期刊网:http://www.cnki.net 可查询,并全文收录。
3、八年超过1万成功案例
易品期刊网站专业从事论文发表服务8年,超过1万的成功案例! 更多成功案例
4、发表不成功100%全额退款保证
易品期刊网的成功录用率在业内一直遥遥领先,对于核心期刊的审稿严格,若未能发表,全额退款! 查看退款证明

- 推荐
- 点击
- 论中国端午节文化在日 01-08
- 采矿工艺技术改造探究 09-01
- 试论当前交通安全存在 05-22
- 试析感悟高水平研究型 03-14
- 儿童个人事务自主观的 08-08
- 血液标本溶血原因分析 03-20
- 中小企业全面信用管理 11-27
- 浅析企业如何防范赊销 05-02
- 基于粗集理论的中西部 09-25
- PDCA循环在急诊护生带 03-15